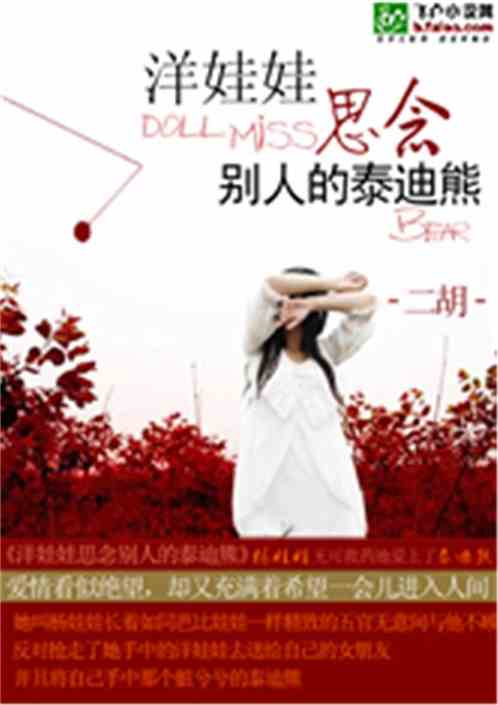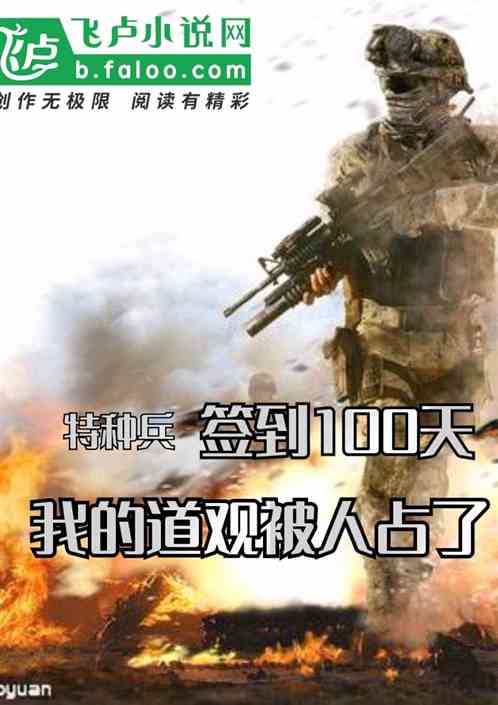我的名字是卡忒琳娜。我是刺客。是的,刺客,不是杀手。
第一次被培养成刺客的时候,被一本正经的告诉我,我们是刺客,不是杀手。那时,我没有因为孩子的好奇和天真而消亡。我兴致勃勃地问教官:“请问刺客和杀手有什么区别?他们不都是为了消灭敌人而存在的吗?”
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教官的眼神很犀利,我害怕面对一场惨败,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可怕的不是教官,而是吓到我脑子的杀气。然后教官抱着我的脖子,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,无视我脸红的脸和无助的四肢。他脸色铁青,说:“我不管你是谁,也不管你有什么天赋,但如果你在我再说话的时候打断我,我就无情地杀了你!”
我拼命挣扎,但没用。我只等教官的脸色稍微差一点,然后就忽略了我的身高。我只是轻轻收回手掌,让我失去平衡,摔倒在地上,屁股疼。只是这种痛苦的感觉刚刚升起,就被我颈间生死之间的窒息所取代。我不再理会自己的形象,呼出一口气,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,活着的感觉,还有呼吸这个小东西。从此,我彻底告别了好奇心和求知欲。生与死之间的巨大恐惧迫使我从未激起一丁点不该有的情感。
我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,第二天自己找到了。如果能再活一次,我宁愿没有这个答案。
小时候,父亲现在不是元帅,只是将军。德克萨斯州有十几个这样的职位。听起来将军的职位不太好。事实上,在德克萨斯州这样的军政府中,将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人物。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他造反,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立即陷入分裂的内战,没有翻身的可能。也就是说,一个将军足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而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,当然不可能满足于只有一个配偶。这么说可能有点难听,但在我看来,这十个女人,包括我妈,跟动物的配偶没什么区别。他们每天要做的就是等着我父亲走运,以此为荣,然后谋生。从他们踏进将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,他们的生命和灵魂,包括他们的孩子,都只是我父亲的工具。
工具,是的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五岁的时候,刚表现出一点暗杀的天赋,就被人给了一把匕首,送到了训练暗杀的组织,我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妈。
她只是跪在我面前,保持清醒,平静地看着我,眼神中没有怨恨和责备,仿佛这一刻我拿着的是一本书,而不是一把匕首。我似乎并没有准备要杀她,反而更像是在给她背诵我刚刚学过的课文,等待她的夸奖。
我双手颤抖,手中的匕首几乎失控。心中的恐惧和愤怒迫使我忘记了昨天的教训。我对着教官尖叫了一声,扔下手中的匕首,跪在妈妈面前大声抽泣。
在我旁边,还有另外九个孩子同时和我一起训练。他们的父母跪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任务是杀死离他们最近的人,就像我的一样。他们的表现和我没有太大区别,只是哭着扔掉了手中的利刃。一个孩子甚至大胆地喊道:“你在开玩笑吗?这是我妈妈。你知道吗,小时候下大雨,发烧到不省人事的地步。我妈光着脚背着我在雨窝里跑了半个小时,带我去诊所之前我都数不清我妈摔了多少。现在,你想让我亲手杀了我妈妈。这怎么可能?”
他的叫喊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记忆,但我不敢再说一句话,因为下一刻,教官突然走到他面前,一把剑插进他的手里,抓住他的手,一头扎进了孩子母亲的心里。在扑哧的声响中,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。他愣了一下,慢慢低下头,他的母亲一脸悲伤,然后疯狂地试图摆脱教官的控制。
教官放开了他的手,然后用一只硬脚把他踢到了一个角落,没有理会他。不知什么原因,孩子只是抖了几下,就没有声音了。旁边的几个警卫上前看着他,向教官点点头。教导员讥笑他,看着剩下的九个孩子说:“违抗命令者,死!今天我就破例告诉你,在你父母和你之间,要么你杀了他们,你活下去,要么我帮你杀了他们,然后你也死了!生或死,自己选择吧!”
我看着被带走的孩子,突然心里感到一种深深的悲伤。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?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,更不用说自己的死亡了。甚至我的生活也不受我的控制。我躺在地上,任泪水流淌,心里想,如果我就这样死去,也许是好的,总比这样活着好。
我的手突然被妈妈抓住了,我有点迷茫。看着一如既往温柔的妈妈,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。如果我没有暗杀的天赋,也许她就不用死了。即使她只是像配偶一样待在将军府,也总比死了好。她现在还不到二十五岁。突然,我有点恼火,甚至讨厌自己。我坐起来哭泣。我妈妈突然去把一把锋利的剑放在我手里。我冷冷,但我的母亲突然握紧我的手,让它向前。她让锋利的剑深深地刺进她的心,看着她的脸痛苦地倒下。
匕首砰的一声掉在地上,我看着自己的手,双腿颤抖着,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。我躺在妈妈的身上,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,妈妈的衣服都湿了。此时此刻,我的耳边正好回荡着妈妈的呢喃:“代替我活着,卡忒琳娜,一定要活出精彩的人生,否则,我怎么配得上妈妈的努力?”
母亲的气息渐渐消散,而我只是像木偶一样坐在同一个地方。虽然我母亲的血沾在我脸上,但我没有任何想法去擦拭它。这时,我的耳边只有教官平淡的话语:“灭绝人类,这就是刺客。为了消灭敌人,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凶手只是最低级的刺客。”
灭绝人类,这是刺客吗?我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个刺客天赋像诅咒一样?我知道刺客和杀手的区别,但如果生活可以重复,我宁愿没有这个答案。
我学习了三年。按照我的实力,应该是9级刺客。虽然不知道这个等级是怎么划分的,但是我清楚的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刺杀教官,这是一种生死之间的第六感。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,也没有心思去追寻。我只是默默地把匕首插进教官的心里,看着他痛苦地倒在地上,告诉我这个高度。
他去世的那一刻,我的三个同伴都在哭。他们不是悲伤,而是兴奋。他们最终为父母报了仇,忍受了三年的屈辱,最终杀死了逼迫他们这么做的反派。可是,为什么心里没有一丝涟漪?我既不悲伤也不激动,只是麻木,仿佛死亡不是我的杀母仇人,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使命目标。
我学习了三年,在此期间,我杀死了37个人,15个六七岁的孩子,9个四肢健全的成年人,3个身体残疾的老兵,2个大肚子的孕妇和8个垂死的老人,包括得克萨斯人、安祖叛军和来自爱奥尼亚的难民。我的成绩是最好的。每一年,我都受到组织的奖励和父亲的表扬,但我的心就像这一刻,没有激动,只有麻木。
在接下来的八年里,因为成绩优异,我的任务数量变得很少,任务的难度开始增加。我的心渐渐变得像一块石头,忽略了痛苦,忽略了感情,忽略了生死,忽略了一切。我心里只有任务目标。即使任务目标是我的姐姐,我的父亲和我的同伴,我也不会犹豫。我只是有一个人形武器来杀死任务目标。
我妹妹,很抱歉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,因为我还不想被她吓呆。不像我,她小时候能说会道,长袖善舞,和两边的人说话。她的父亲开始把她培养成一名外交官,为了从敌人那里获得情报,她愿意做任何事情。在这一点上,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钦佩她。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只要是她处理的任务,没有人失败,尽管有人抱怨她出卖血肉获取信息的行为。我曾经在一次任务中见过她。即使她的外貌和她小时候相比变化很大,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,让我认同她的是眉间的麻木,和我的完全一样。我暗暗点头。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合格的。
然而,如果你沿着这条河走很长时间,你不能让你的鞋子保持潮湿。在从一名弗莱雷机器人外交官那里获取信息的过程中,这名外交官要求她用一把奇怪的魔女剑发誓,她不应该泄露这个秘密。自然,她什么都不允许。骂完之后,她还是把资料交了上去。然而,在誓言强大的自我攻击下,她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怪物,干枯的绿色头发像稻草一样,三角形的眼睛,扁平的鼻子,獠牙和细长的舌头,胸部以下覆盖着黑色和蓝色的鳞片,她的腿变成了蛇尾巴,她是一个独自站立的蛇妖。
她失去了获取信息的能力,被军方流放,但她天生坚强,所以她选择潜伏在诺克萨斯和爱奥尼亚岛之间的守护者之海,威胁随时随地攻击过往的爱奥尼亚船只,而诺克萨斯军方则向军政府索要大量军费驱逐所谓的美杜莎蛇妖。直到很久以前,我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,但我的心还是像以前一样麻木,没有悲伤和快乐,吃,杀,吃,杀,没有任何影响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