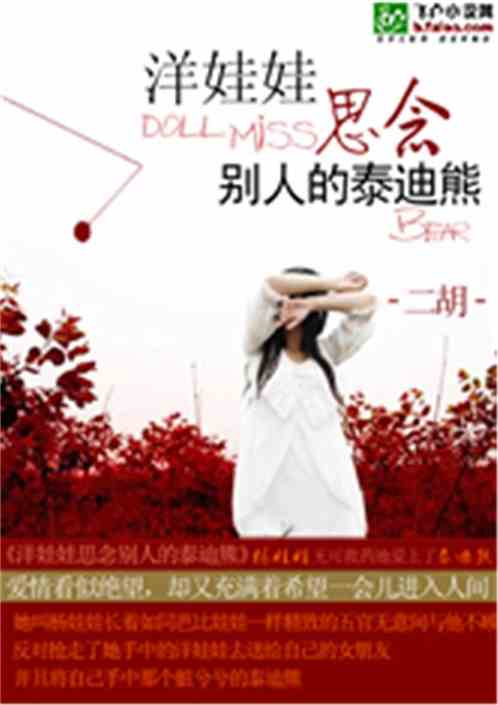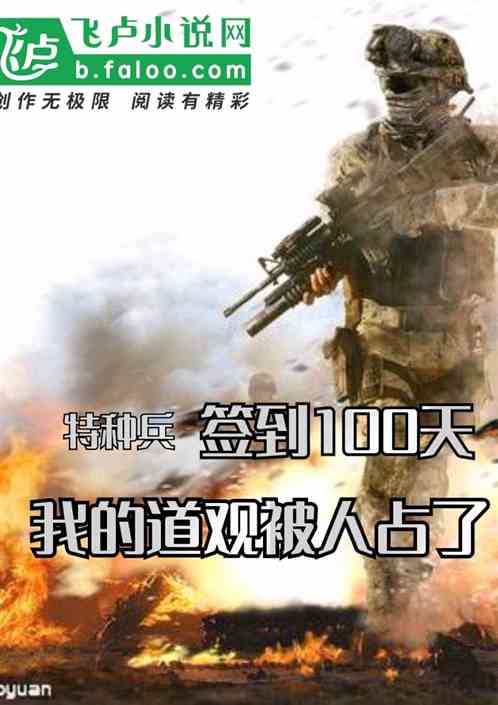我想我醒了。
他瘫倒在床上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。伸出左手,揉了揉眼睛周围的黑线。这种类似按摩的动作,对他来说远远谈不上睡眠,因为精神衰弱而疲惫的神经也觉得舒服。
该起床了,虽然他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。
就像一只死章鱼在城市里伸展开来。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,像蒲公英一样散落在城市各处。有人称他们为垃圾佬,也有人称他们为流浪汉。
他更喜欢称自己为清道夫。听着很爽,让我觉得行走在天地间很侠义。
他找到了一件干衣服。昨晚,他又浑身是汗。一只手拉开旧的木制储物柜,另一只手伸进去,徘徊在两片食物之间。最后,他闭上眼睛,随手拿出一袋普通的饼干,放在小桌子上。
撕开饼干袋,闻起来像吸毒。因为害怕食物残渣掉在地上,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下,一块一块地嚼着。对他来说,每天的吃饭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这和普通人是一样的。
对于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来说,他们的工作就是使用更少的资源,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生存。
这个观念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生存信条。他只需要把这些话封在脑子里就能活下去。
优秀的清道夫。
所以他决定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单手门,你今天去哪?
你今天为什么不多杀两只动物?
他唯一能得到安宁的时刻,就是耐心等待猎物咬死的时候。
对于拾荒者来说,尽量不与其他拾荒者发生争执是基本常识,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恶人。
原来这里曾经有很多拾荒者,有的因为大打出手被打死,有的因为大打出手被打死。他们受不了这种环境就跑了,也有人因为适应不了拾荒者的生活而死了。
生者可以拥有死者的资源。
如果达尔文还活着,他和他的父母会高兴地叼着烟眯着眼打麻将。
因为他赢了。
走在街上,他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在尖叫。
女人?这里不应该有女性,甚至女性生物,甚至是食腐动物。这就像一盒臭豆腐里不应该有蘸酱的意大利面这种普遍的道理。
他的第一反应是后悔做了这个比喻,因为这会让他想吃这两种食物。
第二反应:这里应该是安全的,至少在数百小时前的时间线中,直到一秒钟前。
女拾荒者不能住在这个地方,这样尖叫,会引起所有生物的注意。
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清道夫,这个被所有死了跑了的无家可归者的生命所证明的称号,让他不得不去看看。
人的方便就是哪里有物资,更何况这些人可能会有伤亡或者减员。
吃黑是舞台上最完美的戏码。
他很自然的抖了抖弩,试探性的朝那个方向走去。
大概从声音来源来看,应该是这个小区的三栋别墅,看守着的铁门早已被击中或者腐朽倒塌在地。
电视上可以看到西式全木白房子,窗框上插着零散的玻璃。
之前路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场景了,因为太破旧了,他也没进去。
他选择了其中一栋看起来相对完好的别墅,打开那扇已经无法使用的门,像一个女孩拎着婚纱的裙摆,一步一步慢慢扫视着整栋房子。
女子第二次没有叫出声,还是另一个拾荒者巧妙的堵住了她的嘴,让他很难准确定位。
我脚下的地板开始摇晃,窗户上的碎玻璃开始掉落。他们来了。
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产生的,但似乎他们生来就对人类怀有强烈的仇恨。他们是只为猎杀人类而生的生物。有人说,地球深处的人们清扫污染源,是为了重获健康的环境。还有人迷信地说,死去的灵魂是孤独的,打开了十八层地狱的大门,想要和活着的人融合。
现在他已经顾不上补给了,只好找个地方把自己盖起来,把自己盖起来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向卧室深处。房间不小,但布局极其简单。阳光像糖纸一样照在又高又厚的床上,一个小小的独立衣柜立在灰白色的墙前。除此之外,没有其他家具,似乎在炫耀主人极其愉悦的生活节奏,但房间里所有的平面都被一层肉眼可见的灰尘覆盖。
他摸了摸衣柜,脑子里有了主意。与此同时,几声枪响像是鞭炮声,然后就消失了。男人心里的一震让我又恢复了平静。
他拿起背包里的防毒面具,把堆在衣柜里的衣服全部拿出来,把衣服像羊肉串一样摊在床上的木衣架上。在0: 01祈祷脚下的黑色大理石足够结实后,我从包里拿出一捆绳子,简单地绑在衣柜周围,用力一拉。衣柜的一角完美地贴在床上,衣柜的轻质材质和衣服的垫料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。
男人蹲下,拿起绳子,随意一扔,指尖打开一扇柜门。双脚微微一歪,你就从堆积的灰尘中溜进了衣柜。你抓着钢管,踩着橱柜的缝隙,像风中的旗帜一样挺立,又像被追捕的索莎娜一家,躲在阴暗的角落里。
剩下的只有坚持和祈祷。
他们的气味透过裂缝飘了进来。
就像牛肉撒上牛奶,露天放几天一样臭。
这东西是他军人身份的唯一证明。
当时二班长就把这个东西扔进了怀里,因为虽然窝还很远,但是他一直在抱怨他们臭的恶心。
整个房子在他们的脚步下颤抖,仿佛整个房子都有了生命。
现在他比以前冷漠了一点。
好奇害死猫,他靠本能和技巧活了下来,他在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,至少几分钟前是这样。
他慢慢地吸气呼气,像一只沉默了一千年的老乌龟。
有人遇到麻烦是一回事,有个女人遇到麻烦是另一回事,有个女人能和他说话又是另一回事。
至少刚才他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和他说话的女人。
只有能和他说话的女人才会因为惊讶或者害怕而尖叫。
男人其实我本能的想避开。这不是好事,而是各种意义上的坏事。
他遇到了其他单身女拾荒者,眼神坚定,行动果断,冷静坚强。
在徐如林,风在肆虐,侵略在肆虐,而山却纹丝不动。
门被撞开了。
他们中的一些人走进房间,他可以听到床上的布被刮擦的声音。其中一个停在衣柜旁边。用那双爱德华般的指甲敲着木板,一下子捅进了衣柜。像马戏表演一样惊心动魄,姑娘进了箱子,高帽子一样身手的先生拿起一把细剑就刺了进去。盯着面前的细剑,女孩甚至能看到肌肉的纹理和黝黑皮肤下的血管。手从中央戳了进来,男人一手抓着铁棒,另一只手撑在一个角落里,像森林中的泰山。
手马上搅了起来,指甲像猫的胡子一样探索着密闭的空间。
玉帝佛祖观世音菩萨耶稣基督上帝救了我的命。
虽然他很想把这只手打掉,像门徒中的傻侄子一样。但是他没有锤子用,也没有空调给他立足之地。
“我真的死有余辜。可能是法官派我来收我的。”
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可以总结的,他不动手,他们不会知道这里一定有人。
他仍然不确定他们如何感受人类的存在。
声音,那是肯定的。它们的群体在听到声音后发出撞击声,以识别猎物的存在。虽然近距离看起来不是特别敏锐。
非常奇怪的听力。
当他在一个定居点时,他听到谣言说噪音会使他们痛苦。
但后来这种说法消失了,因为拿着喇叭出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
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慢慢等,只要他不死,就能活下去。虽然他戴着防毒面具,但这就像在他的鼻子里塞了一个小号,但他的呼吸现在被他们翻箱倒柜的声音掩盖了。
突然,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。
他们被发现了,否则他们不会停下来。
突然的停车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他必须摘下防毒面具。刚才的防毒面具可以让他不头晕,但却像小号一样扩大了他的呼吸和气息。
他屏住呼吸,用借来的手慢慢摘下防毒面具,就像在进行一场精细的外科手术一样小心翼翼。他尽量避免发出任何噪音。否则会被整个集群发现,在保持意识的情况下被撕成碎片。他见识过他们杀人的手段。运气好的话,他会把头转几圈,把脖子像麻花一样扭到脊椎上,或者把头压碎,或者把四肢活生生扯下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直接死掉的人是最幸运的受害者。那些运气差一点的会被抱回窝里,会遇到什么都不知道。
好了,摘下防毒面具的过程不算太长,也不算惊险。
他慢慢地平衡了呼吸的节奏。
空气不臭,不臭。这与他的团队攻击他们的巢穴时他所做的相比。
当时他在四五里外就能闻到。
他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他们走得很慢,好像是为了避免发出任何声音。在他们进来之前,他们制造了很多噪音,在壁橱里都能听到,但现在他们像爬行的猫一样移动。
声音慢慢在客厅里聚集起来。
然后就听不清楚了。
他感到安全。
然而,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
地板又在摇晃了。你走了吗?
在不确定是否安全时,他不敢轻举妄动。
不,我没有离开。我发现了一些东西。
另一栋别墅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,应该已经找到了。
一般这种别墅都会有一个位置不固定的储藏室,有楼梯连接地下室。有经验的拾荒者会装饰或隐藏下层楼梯的门,使其更加隐蔽。
现在看来,隐瞒已经失败了。
伴随着声带传来的嘶嘶吼声和绝望的哭喊声,响了起来。枪声击伤野兽后咆哮的女人们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。
混乱持续了半分钟,之后腐烂的气味随着越来越远的混乱集群而消失。
现在应该安全了。
但他不敢太放松警惕,
出来后,他双手放在膝盖上直起身子,然后直起腰,勾肩搭背。先把散落的东西放回包里,再捡起扔在地上的弩。直到那时,我才慢慢地探索这个房间。
一眼望去,一片狼藉,像是活猪屠宰现场。破旧的木质活板门上被打了一个大洞,木板和木刺散落一地。就像被一个大妈暴力推开了促销店的门,她下了楼,像一个溅了红漆的金属架子斜躺在楼梯上。血红色的血浆和残留的肠子、肝脏和一些碎骨混合在一起,涂抹在地上,一勺粉红色的东西在一系列与一些皮肤相连的肋骨旁边。黑色的头发挂在粉色上,沿着肠子可以看到一只粉色的鞋子。看起来像是啃了一半的棒骨还穿着粉红色的帆布鞋。横截面全是血肉,脚下是一堆纸箱子。还有一滩人类的遗骸,整个地下室都弥漫着屠杀后残留的血腥味。
他又戴上了防毒面具。雾蒙蒙的景象会让他觉得不那么真实。如果是第一次看到,他可能会尿裤子,但现在只会让他觉得东西太散,影响寻找物资。
倒下的金属框架周围散落着易拉罐,地上还有床垫。
这应该是女性拾荒者的住所。
太奇怪了。我以前从未在这里见过任何人。
我不应该。我应该没有犯错误。他拿出一个袋子,把沾满鲜血的罐头食品放了进去。
手上的血感觉不好,黏黏的。收完易拉罐,他把手放在纸箱干净的地方擦了擦。他皱了皱眉,这个手印有点像去公共厕所没纸的挣扎。于是他又把手背擦了一遍。
清洗后,他打开了纸盒。
纸箱嘎吱作响。
不,它不是一个纸板箱。
他斜着看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