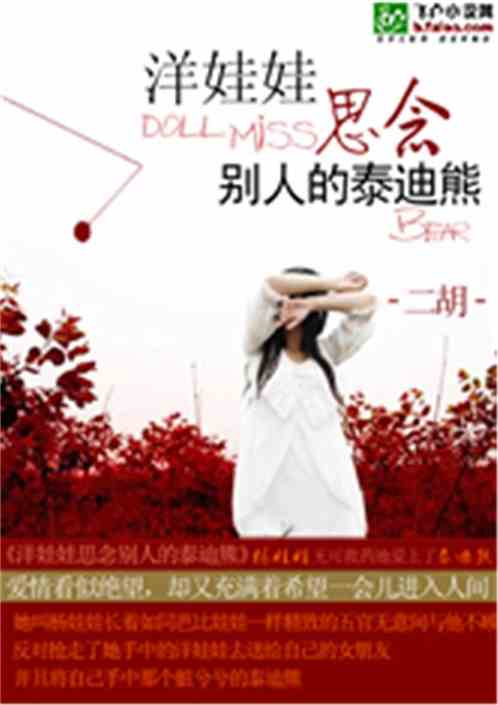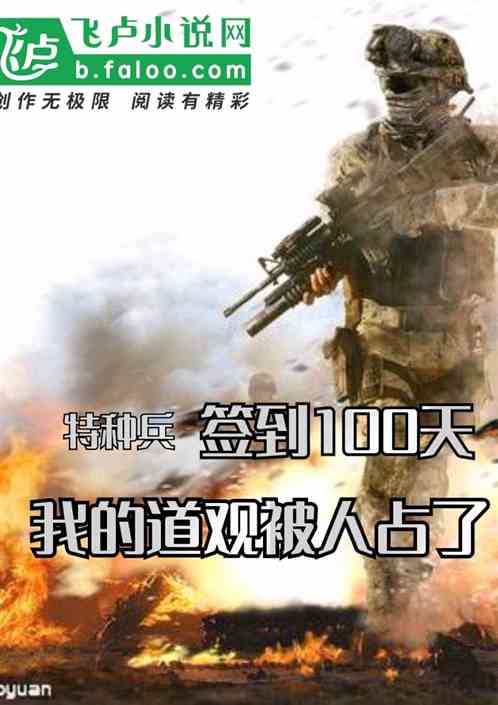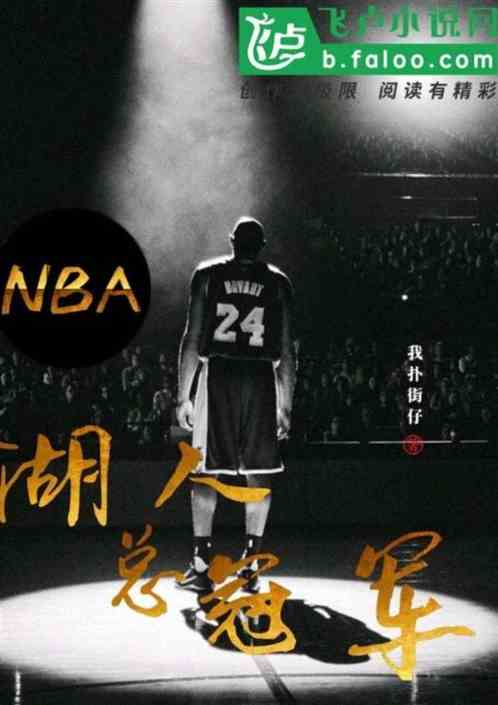我被监禁是因为我杀了人。。。。。。
睁开眼,白光刺眼,我眯眼用手遮住光。我身体的疼痛机制刚刚被打开。我下意识的摸了摸后脑勺,手指先感觉到了一些粗糙布料的触感。我再努力一点,头都要裂了。
“嘶...啊……”我使劲喊出来,只有这样,我才能分担一些我的痛苦。我感觉过了几分钟我才稍微放松了一些,也不知道是疼痛减轻了还是身体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疼痛。之后,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恐惧感。那是对死亡的恐惧。天气太冷了,我浑身发抖。我蜷缩在角落里,平静了一会儿。我开始环顾四周。
后脑勺应该受伤了,包着纱布,眼睛适应光线后也没觉得白光刺眼。我反而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,头顶上散落着七八个洞,硬币大小。透进来的白光好像是荧光灯,是唯一的光源。我后脑勺上粘在手指上的血,只有在极小的光束下才能看到。我被囚禁了?我为什么被囚禁?我做了什么?我是谁?
我失忆了?我不记得我的名字了。为什么我会在这里?我努力回想自己是谁,越想越头疼,仿佛有颗炸弹在脑子里爆炸。我咬咬牙,尽量不发出声音。我的意识告诉我,如果我似乎发出声音,我会立即死去。疼痛抑制了我对自己身份的好奇。
几分钟后,头痛减轻了,我开始观察这个房间。应该是一个房间。它四面有墙,是一个长宽约七八米,高三四米的方形房间。我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。幸运的是,只有四肢感到无力,四肢没有受伤。
我试着敲墙,用力抬起手臂,握紧拳头,用中指节“咚…咚…咚”地敲墙。
声音低,墙壁的质地应该是水泥。透过弱光的眼睛远远望去,角落里有一个马桶,脚下有一个凉席,凉席上有被子和枕头。我绕着墙走了一圈,感觉到一个冰凉的触感。这是一扇金属门。门与门之间没有空气流动,也没有光线进来。其高度和宽度与普通住宅门相同。我用手探向门把手,试图打开门,这是唯一的希望。我握紧把手,用尽全身力气去推拉门。僵持了很久,饥饿感慢慢来了,但门还是打不开。
根据本告诉我的能力,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呼救。
“救命…敲门…敲门…有人…救命…敲门…救…命…啊…”我拍打着门,大声呼救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的嘴唇开始开裂,手指开始疼痛,我大叫,跳动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我用尽最后的力气,踢门,“咚……”的一声回荡在耳边。门根本没动,却触碰到了我已经受伤的伤口。
我蹲下来,头过头顶,背靠着金属门。“呜呜呜……”我哭了一会儿,缺水,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恐惧、痛苦、寒冷、饥饿、黑暗、孤独和无能为力。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在这一刻交汇。我把头靠在膝盖上,现在几乎没有力气哭了。口渴驱使我爬到马桶上,打开马桶水箱。还好马桶水箱里有水。什么耻辱,什么污秽,在生死面前都是一文不值。我用手捧着水喝。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甜的水,虽然我不记得我是谁了。我的渴解决了,我的饿还在,我的虚弱让我和马桶一起睡。
我做了个噩梦。我眼前看到的是又红又臭。有一个人。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,那么熟悉却又陌生。他的蓝色衬衫上沾满了鲜血,就像几个恶魔在他的衬衫上跳舞。男人们用刀砍人。那是一把不锈钢菜刀,在白光的映衬下散发着冰冷的味道。我往地下看,看到一大一小两只脚在地上。每砍一刀,都会溅一个人一身血...这时,他转头看着我。我看不清他的脸,但我知道他的脸绝对是恶魔般的...
醒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一坨菜,菜里都是香味。我疯了一样爬到门口,手里拿着食物啃了起来。我开始把米饭和大白菜全吞了,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的身体不允许我细细品味,只是本能地补充能量。我吃饱后,在金属门下面发现了一个30厘米长,10厘米宽的区域的缺口。我试着推开缺口,但就是推不开。应该是用来给我送饭的。外面好像锁了。
抓我的人会给我食物,帮我包扎伤口。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囚禁,但是现在看来我是不想死了。但我这样下去,和死没什么区别。想到这里,我再次瘫倒在地上。为什么,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。
我的肚子饱了。我看着天花板上的洞,就像七个月亮同时挂在天上。在洞外,我只能看到一盏日光灯。通过不同的孔,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荧光灯。灯的大小应该和篮球差不多。荧光灯旁边除了白色的天花板什么都没有。
我看着天花板的一角。“嗯?”我立刻挺直了身子。
相机!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头在发红光,就像魔鬼的眼睛在盯着你。很明显,摄像头在工作!镜头里面的人知道我看到了镜头,操纵它上下旋转,好像在跟我打招呼。看到这个,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拿什么东西砸这个相机。我掀开角落里马桶水箱的盖子,准备扔过去。相机说话了。
“这是你唯一能联系到我的东西。砸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”那个粗犷的中年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夹杂着扭曲的电子产品。他说的话没有掺杂任何情绪,但我对此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。我不能确定这种情绪大部分是负面的。
“你……你是谁?”我抿了抿嘴唇,放下马桶水箱的盖子,用手擦去额头的冷汗,直起身子掩饰着此刻的焦虑。
声音的主人疑惑地说:“我是谁?”他努力掩饰自己的感情,却又忍不住产生了怀疑。然后停了三四口气,说:“忘了也没关系。我会提醒你你做了什么!”他生气了,声音越来越大。
“我做了什么?冷静点,让我出去。当警察来的时候,我会争取宽大处理……并且处理……”我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,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警察身上,但是想到这个破地方警察就难免虚张声势。
“哈...哈...哈...哈哈的笑声...巨响...呜呜……”
他放声大笑,肆无忌惮,声音很大。笑过之后,他开始哭。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尖锐而收敛,可以清晰地听到擤鼻涕的声音。之后摄像头喇叭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声音,应该是理清了他的情绪。
“你以为你害怕警察?嗯?还是我怕警察?”他的语气变得尖锐。“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惩罚犯人和杀人犯!”他变得如此激动,以至于可以听到他说话时拍桌子的声音。
“我?杀人犯?这怎么可能呢?不,不可能。你快放我出去。我可以解释任何误解。”我不太相信我能杀人。
“我不会这么简单就杀了你。我会慢慢折磨你。你是我的实验品,不会让你死的。祝你好运。”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这几乎让我在心理上不知所措。
“实验?什么实验?我杀了谁?你回答我的问题!”我也开始生气了。这个人已经误入歧途了,还得被当成狗屎实验品。就算我杀了人,也轮不到你来惩罚我。
"……"
“你好!”
"……"
“你说话!”
"……"
“说点什么!”
"……"
摄像头没声音,好像没了?憋屈,真的憋屈,受伤失忆,被囚禁,饥寒交迫。我能怎么办,我该怎么办,就当别人的小白鼠?但是我能做什么呢?只能迷迷糊糊的睡觉,连时间的流逝都不知道。我会发疯的。
我又压下了砸相机的念头。我用花露水洗了把脸,侧身躺在垫子上。现在只能慢慢回忆过去。也许记忆可以为我的逃离赢得一次机会。
头疼,一如既往的疼,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是头部受伤造成的吗?我不知道,也许是吧。我的身体仍然很虚弱。我躺了一会儿,眼皮撑不住了,就开始打架。
我又回到梦里了。我很清楚我在做梦,因为我在砍人,我自己也停不下来。每次我掉刀,血都会溅到我身上。
“噗”
“噗”
“卡”
是刀落在肉和骨头上的声音。我的身体不受我控制。每一刀都变得机械,每一刀都是残酷血腥的乐器。地上躺着两具尸体,已经血肉模糊,血肉模糊。血顺着地板流到我的脚上。虽然我看不清楚尸体,但我清楚地明白,他们是一对母女。我的直觉和我的过去告诉我,他们是一对母女。他们对我很重要,但我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我看着地上的血,看到了我的身影。我的瞳孔从下到上慢慢聚焦在我的脸上,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。
没有脸,没有鼻子,没有眼睛,没有嘴巴!我看到了无脸怪物!这是我吗?我倒映在血泊中,机械地转过头。“点击。。。咔嚓”扭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,脸垂直于脖子。更诡异的是,怪物没有嘴,但我清楚地看到嘴角肌肉和脸颊肌肉挤在一起,怪物在笑!
“啊”
我醒了,跑去厕所水箱洗脸。然后我坐在马桶上打坐。这么生动的梦真的只是梦吗?如果不是梦,是我的记忆,那我真的是妖吗?然而,虽然两个梦的环境相同,但视角却不尽相同。第一个噩梦是第三视角,第二个是第一视角。奇怪,奇怪。
吓了一跳,我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噩梦中的地方,哦不,更像是我住的不高的地方,因为熟悉,有家的归属感。我在这里开心过,也难过过。这个地方的楼层不高。我记得我总是在电梯高峰期走楼梯。我不喜欢拥挤的地方。噩梦中,除了刀的声音,还有呼啸的风声,一片枯黄的枫叶卡在外窗玻璃和窗框之间。除了枫叶窗户很干净,好像擦窗户也有我的功劳。
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我的目光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走,停留在门口地上的“剩菜”。我走过去拿起一小片吃剩的白菜叶子,仔细研究起来。我不饿,但我只是不想放过任何离开这里的线索。
我左手拿着菜叶,把它交给房间上方洞里稀少的光线。我拨弄着右手的菜叶,最后发现白菜被虫子咬了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