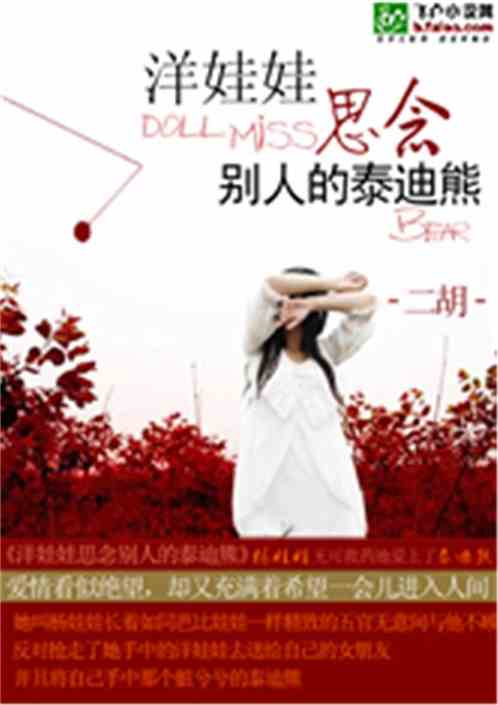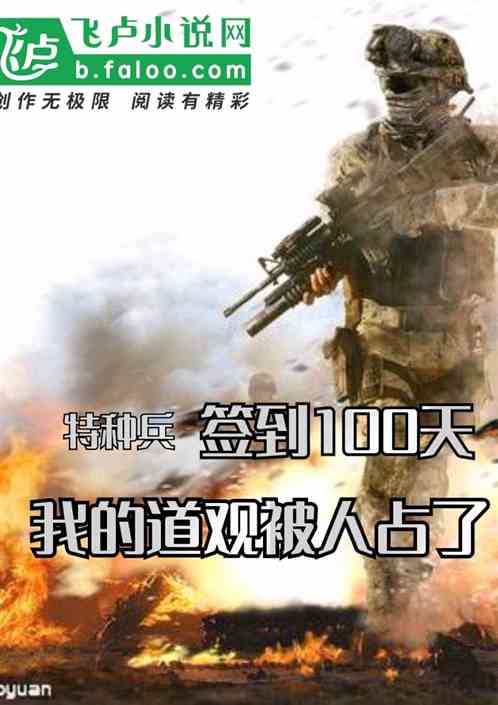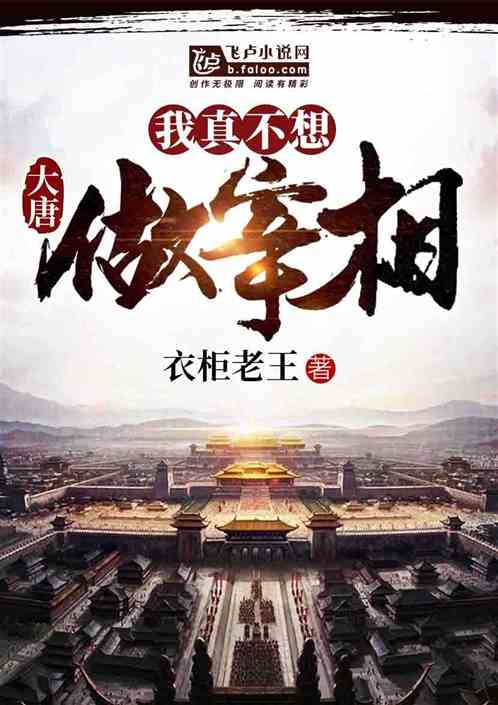眼前一片白光,梦里还留着问题的影子。一阵‘比比’冲进我的脑海,胡乱拉扯着我的神经。我睁开眼睛,勉强吸了口气,瘫在床上,直到第一个闹钟停了,第二个闹钟响了,第二个闹钟停了,第三个闹钟响了。我慢慢起身,摸索着过去三年留下的伤痕。果然...我的身体在几个小时内迅速恢复到三年前的状态。
我知道我第一天上学不应该迟到,但是我没有迟到过700多次,所以我习惯了。我在考虑穿校服去参加那个学校的开学典礼。三年换一次学校,是我三十多年来的生存原则。我拿了一把剪刀,把头发剪短了。时间长不重要。反正三年后就是齐腰长发了。我穿上黑色苏格兰衬衫和卡其布运动裤,拿着几十年打工攒下的钱,毫不留情地锁上了门。虽然这打扮像个男生,但是一个细细的声音就会露出我的本来面目。
站台附近人来人往,但更多的是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。我买了一张去奈良的票。火车一到,我就上了第一节车厢。突然不想浪费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快速结束的生活,突然不想在这种计划好的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出现一点多余的东西。
“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,哇。我深吸一口气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
“竹川大叔,还是这么及时。”我脱口而出。因为几十年来,只有曾经是我生物老师的武川茂夫医生,也只有他知道我身体变化的秘密。虽然16岁的孩子都要叫爷爷,但我一直要求叫无趣的叔叔。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帮我恢复正常,可惜他一次次失败。
“啊,对了,不知道你身体是不是又对上次的药产生抗体了?”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对一切的不耐烦,笑着说。
“对,对,什么药都没用。早上醒来,我又回到了三年前。”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,里面有一种蓝色的药。世雄把这个实验叫做OYSMNSI-13,好像是晚安romaji的第一个字母。这是第十三次实验,但不幸的是,我的体质战胜了它。
“哦...现在我不得不再做一次...可是小李,你这次在学校的这三年打算在哪里度过呢?”他停顿了很久才继续问,我大声叹了口气让他听到。
“嗯,大概是奈良的吧。我去了之后,去了日本所有的大学,我都四十多岁了。”我在电话里吐了吐舌头,旁边一个少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。谁知道他不相信,但这是真的,我足以做他的母亲。我狠狠的看了他一眼,十五岁天真的糖色眼神,大大削弱了威震天的程度。但他马上把头扭向一边,假装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。我知道他还在听,但他从不在乎。我不屑于一个比自己小几十岁的人。当然,我指的是生存的时间。
“哦,到了那里给我打电话。几个月后我会把14号带来。上帝保佑你强壮的身体,你不会抗拒的。如果你抗拒它,你会有麻烦的。”听筒那头立刻传来他的大笑声,车厢里的人再一次惊讶地看着我。我立即按下红色按钮,耳边嗡嗡作响。
“可恶。”我发出嘘声,抱怨。
途中经过两站,坐在那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。我不慌不忙地坐在椅子上,伸直双腿放松肌肉。男孩挨着我坐下,把他的大旅行包放在脚下。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,我低头看着我的裙子——只是更像一个男孩。我闭上眼睛,撅起嘴唇,合上衣服,可能效果不太好。
“那个..”我不知道又是谁在说话,但很可能不是在跟我说话。我的眼睛仍然紧闭着。
“嗯...请问,你是濑户姐姐的哥哥还是...妹子什么的?”我感到有一双手放在我的左肩上。我睁开眼睛,看着刚才那个男孩。
“不。”我叹了口气。我的姐姐和哥哥完全不同。
“哦……”
突然,我只能听到车厢在铁轨上晃动的声音。阳光透过窗户反射出一个个来回移动的影子,我的眼睛追着影子晃来晃去。
“濑户姐姐很好...我只是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,但我觉得你很像她。我哥哥以前追过她,但后来连她的名字都忘了...你知道濑户理沙吗?”他继续问,我盯着他的脸,却想不起任何关于他哥哥的记忆。
“对,那应该是你哥的问题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,感觉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
“那是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濑户的时候,那时我还是个孩子。后来,我渐渐失去了对她的记忆。我只记得她成绩很好,对同学很好。今天看到你,我突然想到了她。”他把头歪向一边,一脸开心地期待着什么。
“学了七八遍的东西再去考当然没问题……”我低声嘟囔着,又一次对自己无尽的生命失去了希望。
“你说什么?”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“啊,啊,我是说...我们到了。”我看着窗外慢慢平静下来的大楼,慌慌张张地说。抱怨自己智商永远长不大的悲剧。
随着一声巨响,火车停了下来,车上的人陆续下来。他提起旅行包,惯性的摇摆着,冲我笑着说:“再见。”我看着他等了一会儿。我深吸一口气,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意一个比我小几十岁的人。
车站附近的人们熙熙攘攘,太阳试图温暖头顶冰冷的地面。随便找了个路人,满脸笑容地问:“大叔,这附近哪里可以租房子或者买房?”
“从这里直走,过了路口,然后左转,然后一直走,一直走,你会看到一条狭窄的巷子。当你转进去,你会看到这么大的房子,有一个尖顶……”大胡子大叔一边比划着双手,一边绘声绘色地说着。但是我一点都不明白。最后,我绕到他说的房子。这房子很宏伟,但无人居住。门牌上写着“灵本”。我走过去按响了门铃。没响两下,有人打开了里屋的门。
一个年轻女人的头从里面探出来,她盯着我看了好几次。
“请问阿姨,这是要出租的房子吗?”我一直觉得叫她阿姨很奇怪。她似乎还不到三十岁。
“你想租?”她一脸惊讶,瞳孔长大看着我。
“如果可以的话,请卖给我,这样比较方便。”我笑着说,心里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她更加惊讶地盯着我。
“那就进来吧。”我终于听到了我想听到的。
房东好心帮我降了价,说卖给我。但是,这个数字仍然不是1978年普通人能攒下的。好在这几十年,我攒够了打工的钱,只是手头暂时不会有钱。经过一番讨论,我决定和别人一起买。因为房子很大,我觉得很值。刚开门的女人看到我从旧背包里拿出一叠叠的钱,更加惊讶。
房东答应我让我先搬进去,但谁知道我是不是可怜一个长得像孤儿的孩子。实际上,我是个孤儿。不能说是幸运,只能说是过着可悲的生活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