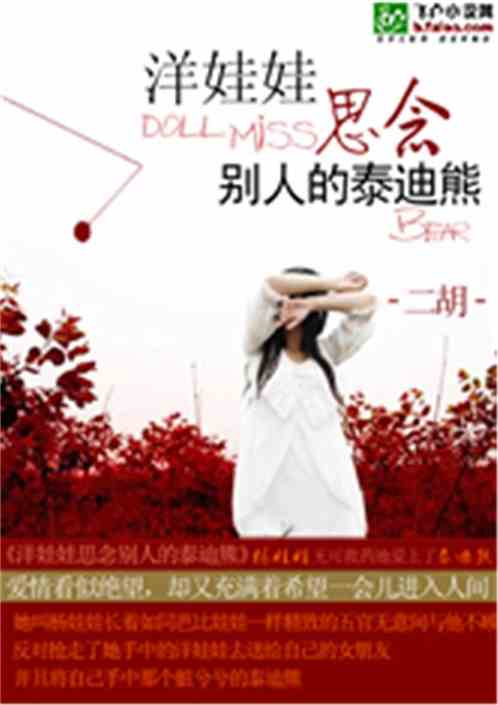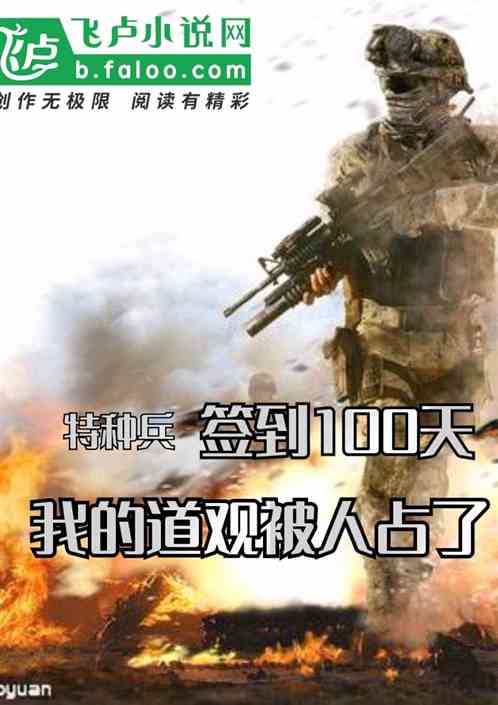静止的沙漏。温暖的木梁。纯白色的沙子从透明玻璃的另一端缓缓滑下。这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。单小纯静静地躺在一张精致的小床上,上面盖着厚厚的棉絮。床单是她最喜欢的用板蓝根扎染的水蓝色纳西布。她安静地躺在上面,像鱼在水中一样。耳朵里还有一个独特的有猫脚印的耳机,有什么东西在静静地流淌着关于古老而永恒的歌谣。
萨顶顶,一个懂让单小纯仰慕的梵语的山东女子,用自己独特而古老的声线描绘着万物生灵。这是一件美好而难忘的事。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首天籁之音。所以她只愿意听梵文版的。
这又是一件已经形成习惯的事情。
丽江。
一个爱情观念和单小纯一样古老的小镇。
爱,爱一个人,是一辈子的事。就像丽江和纳西族一样,是一样的。在单小纯的内心,这是一种对普遍规律的信仰。
丽江,金色的线条,是她的最爱,有时甚至超越了温暖的夜赋予她的美好质感。黄昏。温暖。毛茸茸的灯光下,轻轻捂着嘴唇躺在床上。朱砂的唇色。带着华丽裸的诱惑,她用一支华丽的口红勾勒出浮雕画般的唇线,这是她除了夜晚来临听歌之外的另一个爱好。
黄昏时分,幽静的、绿油油的、湿滑的石板路,有着水汪汪的样子,有着温暖耀眼的色彩,有些刺眼。窗外,偶尔会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用古老的木料做的古乐器,然后并排弹奏着董菁的曲子。
此时,单小纯已经不再躺在那张温暖舒适的小床上,而是选择站起来,以另一种姿态面对窗外的街道,弯下腰,竖起耳朵,静静地听着岁月流淌的天真的歌声。什么时候停的?她不知道。因为内心已经传达了比音乐本身更有意义的生命延续的赞歌,还有远古文明传播的痕迹。
黄色,微弱。然后就是晚上了。在丽江的夜晚,你可以看到清晰的星星。单小纯只有在这个时候,我才会选择慢慢地、懒洋洋地起床,就像隔壁奶奶养的一只叫白纬玲的猫。低低的眼睛,略显贪婪的嘴角,还有一丝腥红的嘴唇。这和白纬玲一样。米优,纳西族的名字,是属于丽江和纳西族的东西,也是单小纯来到丽江后的第一个朋友和最爱。
这样的爱与孤独的灵魂无关,她也一直这么认为。只是单纯的爱,就像第一次遇见丽江,我义无反顾的来到这里,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
单小纯手里拿着一件丝绸大衣。略带甜味的香气。头发有淡淡的蜡味。是糯米的香味。夜晚温柔的月亮河,满天繁星点缀,犹如古阵。头晕目眩,模糊不清。纳西族,一个著名的民族,风俗宜人,淳朴善良,这是她能留下来的重要原因。今夜,月光凝聚成一束又一束。在山下,那里有轻微的雾,我划伤了单小纯的眼睛,受了点伤。
人行道。略滑。一些地面烟雾般的光辉和浓重的气息落在她的肩膀、头发、眉毛和眼睛上。稀薄的空气,散漫的尘埃,坠落的光,还有夜晚朦胧出现的梦幻童话。
青少年。红色连衣裙。灿烂的微笑。洁白的牙齿。干净的眼睛。害羞的嘴唇。微醺的额头。纳西族少年。这是单小纯的一个梦,一个干净清爽的少年,抱着一只叫白纬玲的猫,站在光滑的石板路上,唱着一首普通的纳西童谣。优米安静的小窝在少年的怀里。这是一幅美丽的画。唱歌。青少年。温暖人心的光线从房子后面漏出来。还有一个叫单小纯的女人,穿着扎染水蓝色的布,素颜,玫瑰红的唇色,跳着裸舞,迷幻纯净。
卜,点点。
月初。安静如水。光线一层一层地洒在她薄薄的外套上,烟雾弥漫。浸泡她裸露的肌肤。起来,单小纯慢慢走下阁楼。每走一步都能清晰地听到木质阁楼的吱嘎声。怕吵醒楼下的房东和隔壁养了一只叫白纬玲的猫的奶奶,她脱下了绣花鞋,就像昨天一样。
左手提起绣花鞋,右手握拳。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
出门,赤脚走在又凉又滑的石板路上。很酷的触感。又油腻又凉。和大衣的质地一样。
走过101家,再左转。你可以看到一座桥。相遇和离别可以同时发生的桥梁。一座石桥,在那里相遇和分离可以发生在同一对主角身上。
石桥下,有一条静静的小河。晶莹的涟漪,随时都像单小纯耳机里喷涌的声音一样强大。打她很难受,但这是一种必然的力量和欲望。
把你的左绣花鞋轻轻放在河堤上,然后坐下。你觉得舒服的交叉腿莲花座。就像冥想一样。来到丽江,不知不觉多了些宗教习俗,就像习惯了漆黑的月夜一样。我习惯了光着脚,在一只名叫白纬玲的安静的猫面前自言自语,独自出门。它是一样的。这种习惯性的宗教,让她想起了梦里多次出现的巴书法家的“神仙佛,神仙僧不肯舍法”。
我习惯了虔诚的信仰,习惯了一个人,用自己安静的更华丽的文字去描述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,在单小纯眼里已经成了一种罪过。一些虚无,一些缥缈却又极其真实的罪恶需要被赎罪。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赎罪。
孤独。月份。侵蚀。
我脸上的妆已经褪去了淡粉色。留下透明唇色后,她不再喜欢晚上在脸上涂抹任何不必要的假饰品。自然,就像这条纳溪,这条漓江,是属于佛的。它属于上帝。属于安拉。信仰或许已经变得模糊,但坚持还在。月,阴。星步。就像这个身上扎染布的一般颜色。太棒了。晕。但还是很美。
安静。安静。沉默。
是她来丽江后学的第一件事。那么纯粹的孤独。
类似于花开花落的孤独冷漠。世界仍处于静止状态。只有备用的白沙粒,能透过玻璃另一端慢慢漏出的缝隙,瞥见它们还活着的证据。其他的都不算什么。
安静。渐渐地单小纯变成了沉默的象征。
轻轻剥掉耳机,露出你的耳蜗。然后听着河水流动的节奏,偶尔会走神怀念曾经的少年。
那是一个更遥远的时代。在单小纯还被钢筋水泥混凝土包围的年代。醉了,霓虹灯从来没有让安静的月光有机会照在上海人的面前。对于流星和月光来说,那个如童话般颓废的城市,就是单小纯的故乡。
在断点之前。是醉酒的悲伤。
在断点之后。这是梦的开始。
安静到一种近乎绝望的冷漠。
霓虹灯下的男孩,衬衫洁白如纯水,嘴巴干净。他和这里的纳西族少年不一样。有明显的区别。这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单小纯预测的。或者看到了。
那个上海染病少年还能保持一颗干净的心和干净细致的眉毛,多多少少是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,也超出了她的想象。他还有一个白如单小纯的名字。清纯美好。这和那个冷血少年的温暖不一样。带着最温暖微笑的嘴唇。
这是单小纯对我记忆中少年的第一印象。
不会的,只是到了故事的结尾,那个明净的白衣少年又会回到原来干净纯粹的样子。他站在一棵树下,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手里紧握着一块几乎要融化的带血的糖果,然后慢慢抬起头,轻声对还站在树上的单小纯说,这是给你的,春春。
纯粹。他只是打了她的地址。但是单小纯更喜欢让她叫自己唇齿相依。她从小就爱上了那致命而华丽的口红,爱上了那几乎融化在少年手中的带血的糖果。华丽苍劲的质感。
少年还养了一只叫迪的流浪猫。猫。这是一种罕见的反常动物。白色夹杂着黑色和灰色,更多时候单小纯更愿意相信那是猫在流浪的标志。肮脏。
当她和宿墨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只是一只刚满一个月的小猫。他的母亲和他一样,在限速45公里的街道上被一辆卡车撞得粉碎。
黑色的血留在碾过的地方,像一朵盛开的西番莲大花。那时,皇帝只是一只小猫咪,渴望食物。相扑说,从今以后你就叫皇帝了。于是它带着傅亮皇帝回家了。
当宿墨的妈妈尖叫着从梁迪手里抢过那只略显脏兮兮的小猫时,站在门外的单小纯眼里含着大颗大颗的泪珠。
为什么把人家不要的东西都拿回家?当宿墨的母亲以异常尖酸刻薄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她的眼睛扫了一眼门外穿着水蓝色布衣和一双红色绣花鞋的单小纯,眼里满是讥讽。
在只有5岁单小纯的眼里,太耀眼了,她和比她大2岁10个月零7天的宿墨永远什么都不懂。她只是无助地看着可怜的皇帝被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母亲的手甩出去。
无助无能为力的感觉。带着现在的自己坐在岸边,看着水慢慢流走,却抓不住,留不住。就像那个嘴唇羞涩的白衣少年,最终会越过他的头顶,以一种他从未想过的意想不到的速度出发,光速。甚至那个懒于带走记忆的家伙,在不可知的时间从那棵树上唤回了他的纯真少年,以光速成长,远离了我们单薄的少年记忆。
皇帝。
相扑
还有一个记忆中很难提起的名字,付良弟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