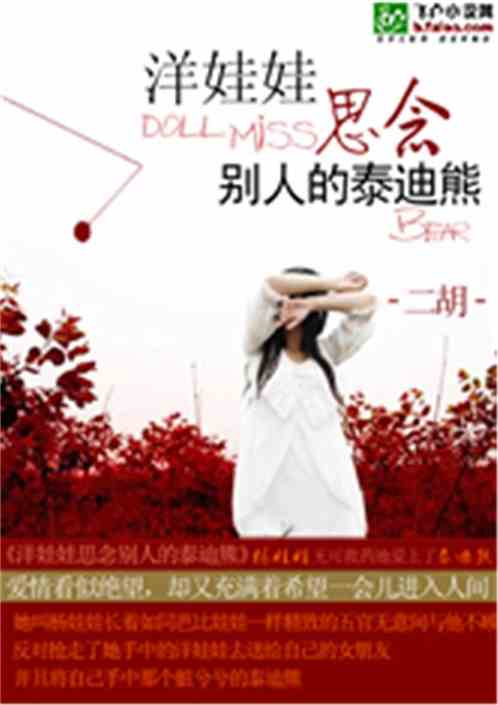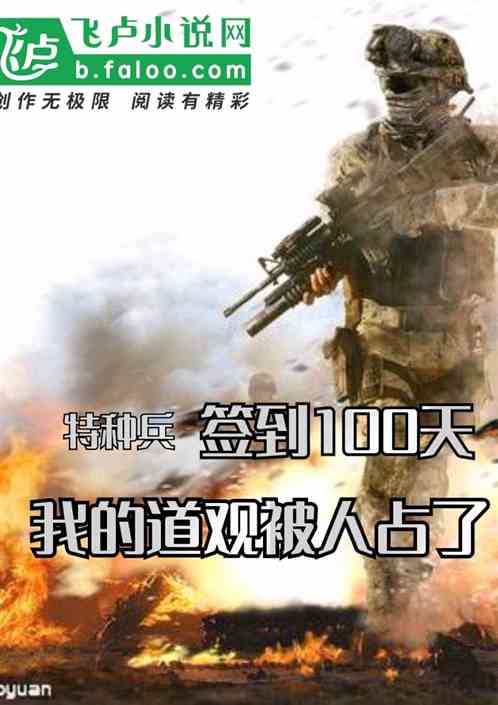我父亲是徐那一辈的独子,除了老婆没有其他小妾。因为父亲说我喜欢一个人就够了,再多一个人就贪得无厌,贪得无厌,难以填补,所以我是整个徐府唯一的夫人。
父亲和母亲喜欢安静和轻松的日子。所以,许家虽然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,但是每天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除了必需品,没有铺张浪费。然而,我是个例外。每个月,我父亲都会邀请赵冉寺的大师来叙府给我讲课,报酬从不吝啬。后来佛堂给我建的时候也是大花,一点都不皱眉。
结果徐家的那些远房亲戚渐渐疏远了我们,后来连年夜饭都不来了。因为自从母亲去世后,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,远离任何人,全心全意照顾我。
但是每年我出事或者生日的时候,总会有人来。
那是我阿姨。她是我母亲唯一的双胞胎姐妹。年轻的时候,我渴望一个贫穷的年轻人。后来不顾家里人的反对,我嫁给了那个穷人。从此,我断绝了和娘家的联系,和那个男人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后来那人不知道吃了什么苦,就在除夕夜起来喝酒。结果他全身突然抽搐颤抖,直接瘫倒在地。那时候姨妈怀孕了,所以睡得很香。结果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老公不见了。她起身往屋里看,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下去嗅一嗅,那人死了,我姑姑吓得晕倒在地。当我醒来的时候,我善良的邻居奶奶正在照顾她。奶奶告诉她,那个人确实死了,连她肚子里的宝宝都没了。姑姑听了一口气,差点背过身去,三天三夜都睡着了。
那时候我妈怀孕了,快临产了。听说我唯一的双胞胎姐姐也是这样的情况。现在我让父亲带她去城西的一个胡同里看望我姑姑,临走的时候给了她很多钱,让她好好照顾自己。如果有什么事,她一定要去徐府找她。
后来妈妈难产去世,阿姨抱着我刚出生的宝宝不吃不喝哭了整整两天,或者爸爸劝她喝碗安神茶,她也只是停下来睡一会儿。
我十五岁的时候,刚到。
姑姑说她没有多少钱给我买那些珍贵的珍珠,翡翠,织锦,所以很久以前就给自己做了一双绣花鞋。因为满屋的客人,很难抽出我的手。仪式结束后,我被要求和她一起回去,说我过生日一定要给我做一碗长寿面。
就在那一天,所有的命运开始转变...
一场不知名的大火吞噬了整个徐府,徐府内包括仆从在内共31人,无一人活着出来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,把徐府变成了一片又黑又臭的废墟。我甚至找不到父亲的尸骨,因为他早已和那些阴暗糜烂的残渣融为一体。
于是我就住在姑姑家,和她相依为命,过着简单平淡的三餐生活。每天和她一起去凤起城最繁华的街道摆小摊,卖她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做的各种鞋子靴子。
那一天,黄昏时分,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,如同月圆之夜的繁星。早在半小时前,人们就开始互相送回家了。
天空多云发白,偶尔有几丝金边,却又轻盈柔和,完全失去了夕阳的耀眼光芒。
夜里来的风特别静,把高楼墙上的旗子吹得笔直,发出响亮的呼喊声。
吴琴的城墙阴沉沉的,看不到日落后的群山,只能隐约看到远处天空中几个凸出的深蓝色轮廓,偶尔划过一个墨痕般的黑点。
“阿姨,要不我们先回家吧?刘叔叔不该来。我们明天再来好吗?”
凤起市和南谯市相比,偏北,所以秋天即使只有半个月,越接近夜晚越冷。因为前几天下雨,连风都好像含了冰。那时候我刚从富家女变成每天要起早贪黑跟着阿姨干活的穷姑娘,有点难受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阿姨那么在乎一双鞋的微薄的钱。
“不行啊,你不知道今天是刘大哥媳妇的生日。他说他必须给他的儿媳妇买一双新鞋。而且,钱都是他给的。他说他今天会来取它。万一来了呢?不要食言,刘家媳妇也穷,日子跟我们差不了多少……”说罢,阿姨抬起脖子,看着大门,嘴里轻轻地嘀咕着“啊...刘的媳妇也是个穷人...一年前,她生了一个孩子,一个月前不知何故去世了,这让他们很难过...真的,罪过,罪过。
当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,神色变得很悲伤,眼眶湿润,感觉一眨眼水就要溢出来了。
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她自己的话,还是我的母亲,还是真的只是刘家的媳妇...
“伯母,再过一个时辰,城门就该关上了,就算他来了,我何不拿去给他?”
“这个…”她转头看着我,话语很不确定,眼神很担忧。
“放心吧,阿姨,刘家渡离这里不远。离市区最多一英里。我去那里跑一趟,很快就回来,这样我们就不用在这里等了,他也不用急着来了。”
她抬头看着城门,仍然有些担忧。
“我去,姑娘。留在这里。”
“阿姨,你不是眼睛不好吗?外面有许多杂草和岩石。绊倒磕碰怎么办?我年轻,身体好,眼睛好。来回跑不是问题。请在这里等候!我很快就回来!”我扯着嘴笑了笑,卷起刘舒订购的鞋子,转身向城外跑去。
身后的阿姨大声喊着“姑娘!小心看路,不要跑那么快!如果刘大哥不在家,他会把鞋子放在他的门下…..”
“是的,阿姨……”
刘舒的家在城外河边的刘佳渡口,那里有大片的桃树。每年三月和六月,河边的整个刘佳渡口都开满了桃花。一阵风过佛,桃花满天飞,满眼都是细小而密集的粉红色桃花瓣,说不出的迷人。
当我到达刘舒家时,刘舒正从门里走出来,看到我来了,他很惊讶。
“刘叔叔,我给你送鞋来了。我姑姑见你没来接,就送来了。”然后我把鞋子从怀里拿出来递给他。
“哦,这怎么好意思!我正准备去拿,想到这个时候你可能早回家了,想到你应该去你房间拿!”
“没关系,正好赶上刘阿姨生日。”
“早该去拿了,又不是我家那头牛跑了!我到现在才追回来!那是...啊...我差点弄丢了!可把我们急坏了!哪里还顾得上鞋子?”他撩起沾满灰尘和汗水的袖子,擦去额头上的汗水,把鞋子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“刘大!你在和谁说话?进来吃饭……”
“啊!是啊!是啊!来了!”听到声音,他立刻转身大声回答,嘴角咯咯笑着好像很开心,样子也越来越憨厚,真像个可怜的老实人。
因为急着回去,谢绝了刘夫妇的挽留,直接跑了回去。
离开刘家渡,直走十几步,然后拐个弯,进入通往凤起城的官道。抬头就能看到巨大的城墙,向两边延伸。
路过拐角的时候没怎么注意,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只是以为是朦胧的绿色。因为黄昏的黑暗,就像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纱。
回来的时候,因为大门就在前面,我就没那么心急了。我走了几步,出于某种原因回头看了一眼。
我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回头,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...
回头看那棵巨大茂盛的槐树,我看到了一个女人,一个穿着桃红色连衣裙的女人。
不知道是她半藏在槐树下,还是槐树的树荫遮住了她,还是天已经黑了,让她看起来很灰暗。
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半明半暗的树下,一阵风扬起她的身体,水纱裙无声无息。周围唯一安静的是远处鸟儿归来的声音,还有槐树茂盛茂密的枝条随风摇曳的细微嗖嗖声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周围是彻骨的寒冷,一股阴冷潮湿的寒意从四面八方袭来,仿佛倾斜的季节已经从初秋变成了深冬,我冷得瑟瑟发抖。
与此同时,一股强烈的压抑气息从树下向我涌来,我抬起头时,正冷冷地盯着那个女人灰蓝色的眼睛。充满了强烈的怨恨和不甘,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鬼神鬼怪,如果心怀怨恨,绝对会是地狱里魔鬼的杀戮和危险。
我想转身逃跑,但我的手脚似乎不受控制,站在远处,让那个女人的眼睛像刀火一样盯着我,仿佛恨不得把我融化进无尽的地狱和深渊,我无法永生。
那种感觉很不好,虽然她没有走近我,但是她周围的阴郁和寒冷,她的眼神,无论哪一种,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说不出的冷热交替,辗转反侧,感觉一颗心在被刀割,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都好像要融化。
于是我马上闭上眼睛,张嘴咬嘴唇。瞬间的疼痛让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清醒过来。与此同时,我腿脚发软,跌跌撞撞,差点扑倒在地。
我没有再抬头看那棵树,也没有在意身边挥之不去的冰霜和空调。我开始向不远处的大门跑去。
进了城,一抬头,看见阿姨正焦急的看着我。她看见我气喘吁吁地跑,责怪我跑得太快。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呢...
之后,我收拾好东西,和阿姨一起回去了。可能是晚上冷,也可能是阿姨日夜操劳过度。于是第二天,她生病不起,患了重感冒,我只好出去找医生吃药,照顾她。
我姑姑家在凤起市一个偏僻的巷子里,离市中心很远,自然离一光的那些药店也很远。但是我听说刘鑫街新开了一家医光,店主说三天咨询的药是免费的。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,所以即使要经过一条非常偏僻冷清的街道才能去那一片光,我还是选择了去,因为有时候没钱的日子甚至比没钱的日子更难生存。
不过还好那天天气很好,阳光明媚,所以我多少还是比较平静的。
义光的掌柜是个心地善良的外地人。听他说,因为他以前行医太小气,不管找谁看病,都要交全款诊费,否则拒绝抢救。后来,他的妻子不幸感染了这种疾病。即使他精通医学,他仍然无能为力。人们都说这是因果报应,于是在妻子死后,他离开了小镇,搬到凤起城,开了一家小义光,但只收了一点医药费,三天没收一分钱,为的是告慰妻子在天之灵,忏悔自己的错误。
因为为了避免有人作弊,店主只给了我三副药,只够用一天。不过,这样也很好。要求人们一次给一只脚是不可能的。大不了多跑几次,不花钱我也会舍得。
回去的时候,不知怎么的,刮起了几阵狂风,早晨的阳光依旧明媚,没有影子。仰望天空,有一团团灰色的、沉重的乌云。果然,秋天的天气变化无常...
路过偏僻冷清的街道时无意看到,因为耳边突然传来木门沉闷的吱嘎声,于是转头看了一眼。
我右边不远处有个院子,不过是后门。屋檐下挂着两盏红灯笼,是家家户户除夕必有的红纱金穗大灯笼。可惜很老了,好像挂了很多年了,挂在下面的金色尖刺有些脱落变白了,露出里面一样的烂木架子。红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,却依然掩盖不了里面的破败。几个灯骨已经露了出来,两个灯笼摇摇欲坠的挂在屋檐下,几乎要断了。
屋檐下是两扇布满岁月痕迹的木门。不知道是什么木头,也许是因为长期的风吹雨打,整个门扇看起来灰褐色,白色。只有靠近房檐顶端的地方,散落着几片漆红色,像干涸的河床,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裂缝。
门前有两级石阶,但磨损的石头已经露出了原本的青灰色,光滑圆润,没有任何棱角。屋檐正下方只有几个小孔,深浅不一,但很圆。估计是经年累月的雨水从屋檐滴下来的。
门两边是两人高的院墙,也是古老沧桑。它们早就失去了原来的洁白如雪,而且非常松散浑浊,很像河中的淤泥土块经过风干晒干。墙上长着厚厚的一排杂草,却因为秋天的到来而显得有些发黄萎蔫,挂在高高的院墙上,露出杂草中覆盖的漆红瓦。
真的想不到还有人住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,被这样的岁月侵蚀,但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,从半掩的木门里传来了孩子的哭声。一个声音,一个段落,我不知道是喜是悲,我没有感情,我只是那样的泪流满面,像夜晚的锣声,吵的人莫名其妙的心烦。
当时我就想,要么是我听错了,要么不是人。毕竟这样的房子以前肯定杀过人,有这样的声音是常有的事,于是我立刻转身离开了那里,头也不回。
我回去才发现,如果真的是鬼,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?如果一个孩子迷路了,不小心进去了,却不知道怎么出来怎么办?
其实我小时候也遇到过几次这种事情,因为那时候很害怕,每天都提心吊胆的,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鸟。只要有一点点不对,我就以为是那些事,所以做了很多坏事。比如我路过一棵树,看到一个小孩正倒过来看着我,我会立刻跑开,不管他的呼救声。比如走在街上,一个婴儿冲向我,一脸惊恐和血腥,我会立刻让开或者踢过去...
我不知道父亲为此付出了多少礼物和道歉,但是最后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我在一起,因为他们总是说我疯了。
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,一个非常奇怪的梦。
我梦见自己在屋外的一个院子里,院子很宽,周围有很多房子,把整个中庭围成了一个方形的子午线。边上是齐腰高的玄关,种着许多不知名的花草,五颜六色,小如拇指,大如菜盘,颜色各异,姿态万千。门廊下挂着许多绿色清新的紫藤树,偶尔有几朵淡紫色的娇小的花,都开在庭上。整个回廊的外部就像一幅又长又宽的春花图。
院子中间有一棵桃树,高大苍劲,葱郁茂密的树荫几乎遮住了大半个院子。
树下有一把藤椅,是青竹做的,看起来很久没做了。因为没有上漆,竹子的绿色和鲜嫩气息都保留了下来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