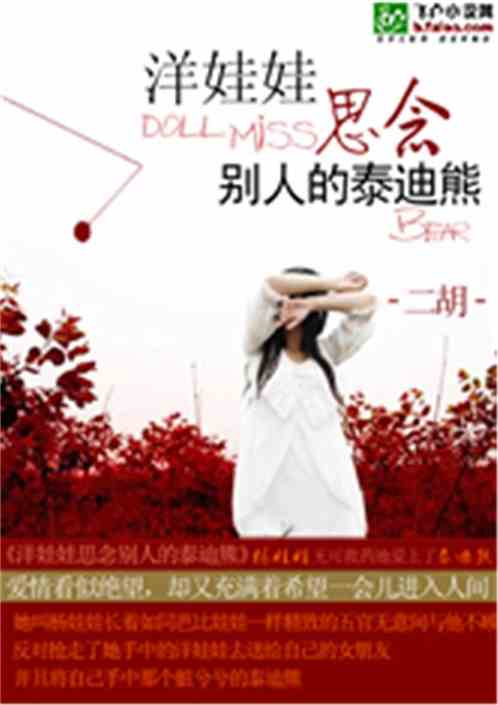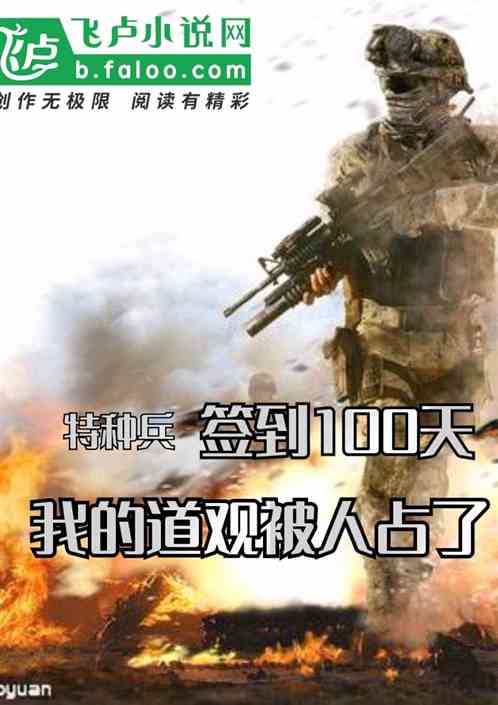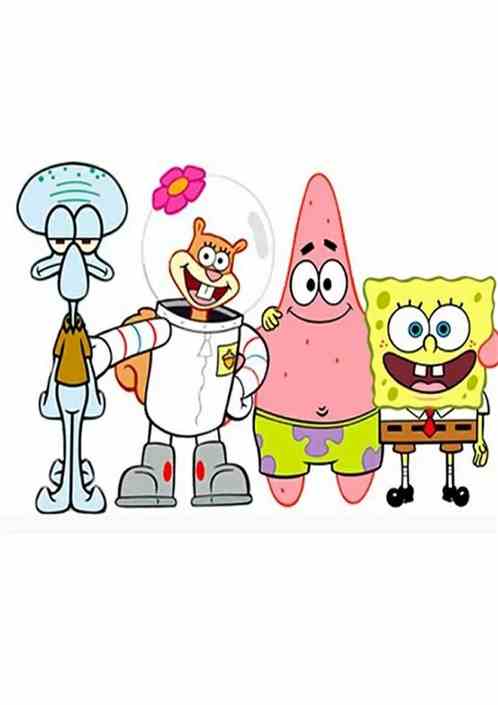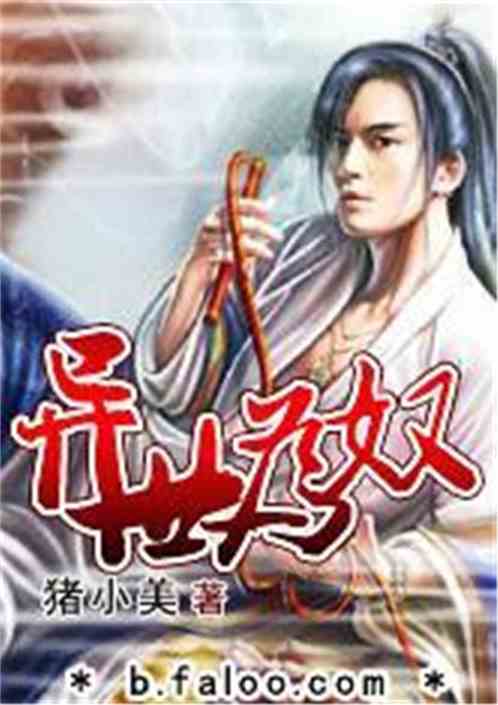房间里很安静。一对夫妇盯着床。她胸前的起伏越来越弱,生命流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女仆们在房间里进进出出,他们的脚步很轻,即使撞到了桌角,也没有发出一声闷哼。丧服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亭子里,白色的窗帘被下面的人挂上,肃穆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房间。
虽然房间里很安静,但是沙沙的声音让我老婆眼圈红了。她上半身靠在丈夫身上,试图伸手去够她女儿喘气,但手却半途缩了回去。
“她还活着吗?”女人抬头问丈夫,丈夫沉默不语。他心里明白,生活再也不会来了,可妻子沙哑的声音还是让他张不开嘴,只能用力捏她的肩膀安慰他。两个人依旧静静的盯着床上的女孩,正厅里有条不紊的忙碌着,井然有序的场景让人觉得整个过程似曾相识,仿佛做过很多次。
“大人,医生来了。”一个女仆把一位医生带到房间里。医生拿出一条白绸子,放在女孩的鼻子和嘴巴之间。夫妻俩急忙上前,死死盯着那条白丝,希望它还能因为呼吸而漂浮。医生微微摇头,为床上的女孩把脉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还是把自己不想从他口中传达的坏消息说了出来。“大人,显微镜还是去了。”
随着这话音落下,整个房间的抽泣声开始从正房传到正厅,侍从们擦着眼泪,依然不忘工作。房间里的女人的尸体倒在女孩的身上,她用嘴咬着被褥压抑着悲痛。古人说:“把新药棉放在将死之人的口鼻上,检查呼吸。若不浮,经查证已过期,诸子、兄弟、亲戚、侍中皆哭。”不哭,你的女儿就不算死了?
在大厅里,侍从们都迈着小步,越走越低。偶尔,轻微的抽泣声会传到郭佳媛的耳朵里。他心里觉得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他的院子里有很多忠心耿耿的人,但后来他想到他们陪他走过了那么多死亡,心里五味杂陈。孩子都死了,要那么多随从有什么用?他们要照顾谁?只是平日里乱吃,家里天天灰尘不落。有什么好擦的?家庭小,没有财产。家里的仆人将来会用它做什么?
他的思绪被赶来的“修复者”打断,修复者就是举行招魂仪式的人。在招魂的时候,受害者会拿着死者的衣服,一只手抓着衣领,另一只手拿着腰间的布,面向幽冥所在的北方。然后他伸着嗓子喊着死者的名字,唤回自己的灵魂。这是挽救死者生命的最后努力。
房间里多了几个服务员,大家都怔怔地看着招魂受害者,喊着小女孩的名字,希望他的小主人醒过来。人长大了,有善恶的狡黠之分,但年轻的时候,没有一个是可爱的。大多数人的善良,在死前最明显。无论他们的地位是高是低,这时候都能真诚地哭出来,人生的一个宝贵时刻就在这里。为你的主人,为你自己,为你死去的家人哭泣,活着好还是死了好?我妈妈有足够的钱在地下消费吗?在反复的呼唤中,这些思想也传到了北方。
郭元甲的妻子姜莽差点晕倒。叫到第一个名字的时候,一阵微风吹过,她鼻子上的纱布动了一下。她迅速摸了摸女儿的脸颊。越来越冰冷的触摸让她知道,逝者已矣,无法挽回。如果她和女儿一起去。第四声接着第五声,每一次刀都扎进心脏。
“我的女儿啊,路上听到就可以回头了。我妈妈在这里等你。我已经观察你好几个晚上了。怎么忍心越走越远?你这么年轻,怎么能这么无情?我妈是不是很没用,让你觉得我做得不够好?快回来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房间里有吃不完的糖果和泥娃娃。妈妈不会让你爸爸每晚都很忙。我肯定会好好陪你的。我的女儿,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你回头看我……”
蒋莽死死咬着白嫩的嘴唇。她听不到回复,心里每一个字都是一声呐喊。最后回复递衣服给她时,她没有摇头,充耳不闻。
“夫人,你应该给孩子穿上这件衣服。”郭元甲接过衣服。他半搂着妻子,低声对她说:“一切都会好的。会好的。”他突然看到妻子略带恨意的眼神,心里慌了。当他再次钻出一个洞时,他的眼睛又变得悲伤起来。在这短暂的一瞬间,江妍是怎么想的?
接下来的工序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女孩的尸体被放在南窗下的床上,喇叭把孩子的嘴展开来装未来的珠子。特制的砂锅盖在尸体上,酒和食物被放在尸体的东侧供鬼魂饮用。
大厅里设置的窗帘把死者和陌生人隔开,全家人换上白色的粗布衣服。郭元甲在书房写了讣告,分发给亲朋好友。书页的离去,带走了郭元甲最后的一丝力量。他捏了捏手中的毛笔,墨色已经晕到了一张白纸的中央。男人终于流下了眼泪,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他,悲伤激荡。
张复的气氛也不好。张轩雄听说前几天郭家女儿病重,这几天不行了。从那以后,他每天都吃不好,睡不好。十四年前,少年时的郭佳媛跟随他上了战场,最终从宁国手中夺得了理想城,两人在此苦苦相守,无法回家。看城市不仅是找国家盯海外市场,也是张轩雄盯国内的方向。
荀国地处内陆和山地地形,境内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。可惜耕地不足,土地贫瘠,外贸路线又被宁国、郭毅占据,对谋国发展极为不利。为了突破新的发展方向,十四年前荀国将军张玄雄出兵攻打望城。望城的港口,大河三角洲的良田,都是他们的目标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