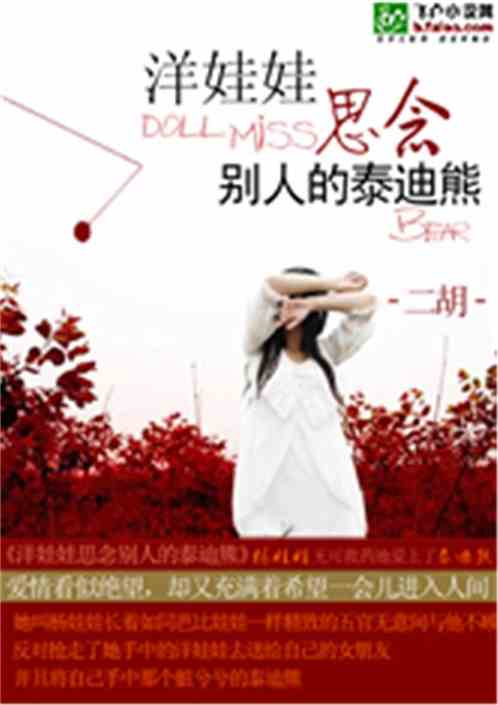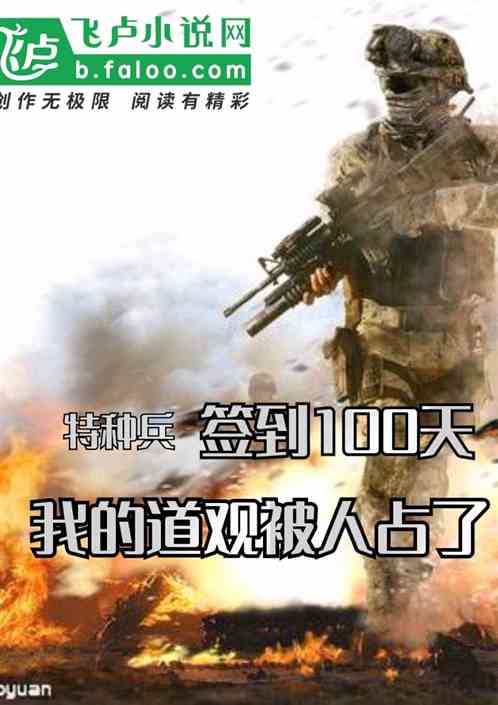“嘎吱!!!"
推开破旧的木门,看着一堆破旧的家具,张垦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十几年前的画面。
想起来了,爷爷去世已经十几年了,奶奶也是。我父亲几年前因病离开了。小时候每天晚上都来找爷爷奶奶要明天的零花钱。
爷爷或奶奶会给你一两毛钱,你可以买棒棒糖或铅笔。一眨眼的功夫,事情就变了,你家也很少回来,更别说老房子了。
随着春节的临近,一家人回到村子里过年。一大早,妈妈就把他叫醒,让他看看老房子,整理一些有用的东西。
张垦我也好久没回来了。我听说爷爷留下了很多东西。
说起张垦的爷爷,大家都无所不知,因为他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,在镇中学当过老师,张垦中学的几位校长也是他爷爷的学生。
老房子只是一个厢房,这个院子里有三户人家。张垦爷爷奶奶住在左边的厢房里,中间有个叔叔住在同一个村子里。右边厢房的一家人已经搬出去了,不知道往哪里发展。反正从张垦记事起就没见过这个家。
老房子分为三个部分,厨房在里面,客厅在门后,客厅用木板隔开,房间在另一边。当时几乎所有老房子的厢房都有这种结构。
原来有很多电器之类的,一个接一个的坏了或者整理了。当你看过去厚厚的一层灰尘时,你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
“好像没什么好整理的。”张垦环顾四周,除了一把老式的破木椅和一个电视柜什么也没有。以前有一些家具,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。
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旧木床。这张床很旧了。有屋顶的木床经常出现在电视剧中。现在估计买不到了,已经磨破了。
没什么可看的。看地上的苔藓。屋顶的绿瓦在漏水,好像以前漏过。
“咦~”
张垦抬头一看,正好看到头顶上有一个半棚子。在一些老房子里,空间很小。为了有一个收纳的地方,我在客厅上方设置了一个搁板,相当于现在的阁楼,人们可以在上面睡觉或者放东西。
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木梯可以爬上去。张垦上面好像有东西,但是没有梯子,只好借一个。
走出厢房,正房的门开着。张垦走过去,我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坐着看电视。
“春福叔,春福叔。”张垦喊道。
老人的耳朵不好。他喊了几句才听到。当他抬起头时,他看到了微笑。
小时候在院子里长大,老人看着他长大。他拉着他的手,坐在一边,一个大声说话,另一个安静地说了一会儿。碰巧他家有一架梯子,他借了它去阁楼。
果然,下面的东西清理了很久,阁楼上面有很多东西,比如泡菜坛子,破陶罐,还有一些破木桶,上面的铁环已经生锈坏了。
这些不是张垦的目标。旁边有一个盒子。作为十里八乡的知名文化人,张垦爷爷每年过年前两个月都会上门贴春联。所以他爷爷最喜欢毛笔,还收集了一些旧书。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他记得他把所有珍贵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盒子里,就像这个漆盒子一样。
轻轻刮掉上面的灰尘。用嘴吹绝对没脑子。刮掉一层灰尘。打开一看,里面有几本书,都烂了。
“怎么会这样?”张垦看着这些粘在一起已经烂掉的书,我闻到一股霉味。很明显,没有打开太久,里面潮湿。
南方最恶心的天气似乎要回到张垦的南田了。回到南田,整个屋子都是水,水滴从墙上冒出来,无孔不入。好几天不舒服,衣服也干不了。
估计有些刷子因为受潮损坏了。
张垦不要放弃,继续找,箱子太大拿不下来,他只能在阁楼里整理,看着已经烂成一团打不开的书,即使打开了,里面的字迹也因为潮湿早就没了。张垦那是一种痛苦。
最终,张垦发现没有一本书保存完好,全军覆没,连毛笔都碎了。
“唉!”
张垦深深叹了口气,整理了最后一层。正当他整理他认为在最下面的书时,他发现下面还有一个盒子。这个盒子不大,类似于笔记本电脑,厚度大约十厘米。
张垦试着摇一摇。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上面有一把生锈的锁。不幸的是,他没有钥匙。张垦试着扭一下锁。也许时间很长。锁已经坏了,他用力拧了一下才真正拧开。
打开锁。打开盒子。旁边有一本黄色封面的书,上面有一把刷子。
这本书看起来并不特别。画笔吸引了他,因为它和画笔的风格一样。
所谓大头笔,如果你见过地狱里法官的形象,应该知道法官的笔是一只只有四寸长却带着大头的毛笔。这支笔张垦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写春联的时候用来写祝福。大厅里或门上贴着大大的祝福,很少有人用。
这支笔乍一看已经用过了,但它仍然很新。
“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物体,可以保存下来供思考。”张垦把刷子收起来,然后伸出手拿起旁边的黄皮书。
“嘿!”
一遇到黄皮书,张垦马上放下,他发现手有点疼。他翻过来的时候,看到刚拧锁头的时候被抓伤了,出现了一个洞,还流了血。
我用裤子擦了擦血。张垦我继续整理东西。回头一看,我发现盒子里的书不见了。
“嗯?书在哪里?!!"张垦回头找那本书,盒子是空的,周围什么也没有。
“书在哪里?”张垦继续找黄皮书,找了一遍又一遍。
不知道为什么,张垦越来越困,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睛。
“嘿!”
头转向一边,在梦里,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低语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