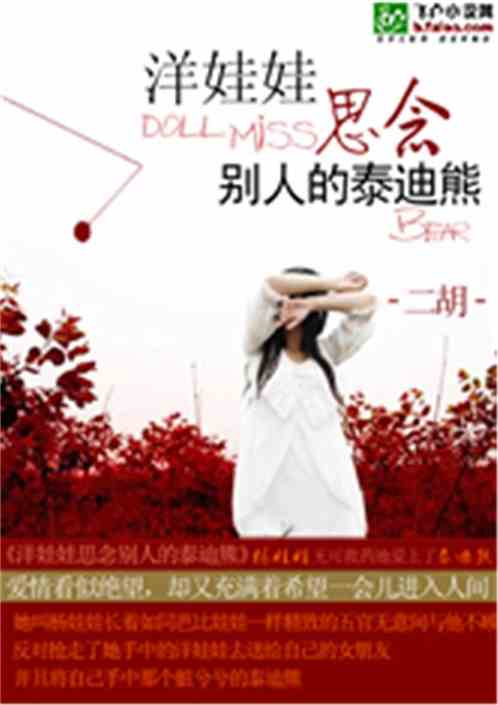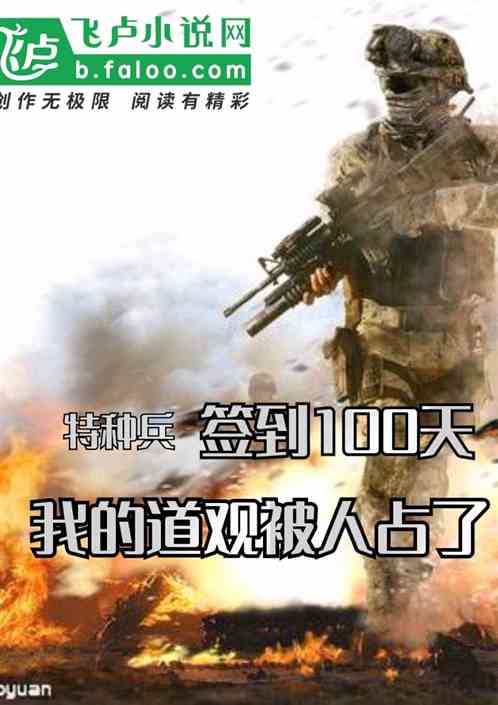横山,地理位置偏向西南,据说在南方。但是北方寒冷的天气经常在横山肆虐,大气候支配着北方顺便带横山。
山多,山高,坑深,植被和植被丰富,尤其是东山,山峰横跨南北。
在离衡阳较近的东山脚下,有一个地方叫东山坳。李富新大宅嵌于洼地,故李富新之名与东山洼地相连。
李富新是个很复杂很乱的人,他认识的人也是,包括对他恨之入骨的好人或者坏人。
周孜倦应该是个好人,好人也会做坏事。
今年深秋的一个深夜,周孜倦独自潜入东山坳,做好准备,放好位置,掏出打火机点燃。“砰!”悄悄的,打火机冒出了橘黄色的火焰,周孜倦用火焰点燃了起爆药的导火索,转身从拐角处退后一步,在黑暗中跑出了五里地。李福信的院子里没有发生爆炸。
周孜倦我想象不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就像上帝躲在暗处保护着他,李福信。
“上帝在保护他。”成了周孜倦放弃的理由。
这个理由很牵强。也许他周孜倦放开了自己。
可能上帝觉得他的想法太简单,不靠谱,无效,所以没让炸药炸了。
。。。。。。
日复一日—
转眼间,季节进入隆冬。
王坡水库周围的山很荒凉,但水库的水很满。用皮薄的话说,这是一个屁股很丰满的女人。
一天到晚面对这个富婆周孜倦我真的没什么感觉,但是对于山路的蜿蜒崎岖我感触良多。我希望有人出现,哪怕是一只狗,这是好事。
寂静得令人生厌,久而久之,山河相视。
反正这里空气清新,风景宜人。漫山遍野的雪松生长在枯草丛中,生长在悬崖峭壁上。如何种植它们真的很难。
周孜倦不难。这水这么多年,说不出有多难。如果孤独属于辛苦的范畴,那么周孜倦真的是辛苦。
周孜倦的女人岳华,在市里的黄金KTV上班,那里各种教学都有,周孜倦的情况很寒酸。不是卑微的一面,而是寒酸的整体。贫穷是一种严重的伤害。
周孜倦我喜欢看水库里的水。我可以看一整天,发呆,思考一些事情。一个人坐在石头尖上看着水面,就像只有水里的鱼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感觉很累,有一种渴望朋友的感觉。
这天下午,阳光和煦,一条大鱼从石头下的水里游了出来,圆瞪着他。“哇——”他身体前倾,钻进了水里,任由水圈慢慢伸展,久久不肯散去。
周孜倦凝视着,思索着,像是得到了某种期待已久的启示,我拿出手机,按下了号码。
。。。。。。
在城里的肉菜市场,圆脸的屠夫接到周孜倦的电话,两次敬礼后,三点钟把肉摊交给妻子,骑上拉猪的破烂三轮车,匆匆向东而去。油腻厚实的脸上闪过等待已久的腐烂笑容。
这已经计划很久了。
说了半天,今晚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目标依然是东山口,直指李福信。
晚上的月光很弱,残缺的月亮被云遮住了,夜很黑,空中没有一丝风。周孜倦和屠夫博三皮在夜色中藏起偏三轮,弯腰一前一后跃过叶秋草丛,跑到李福信的院子里,目的就是为了行窃。
周孜倦一直放不下,酝酿这个动作。
用他老婆岳华的话说,这叫欠,欠了就得还,天经地义。
如果你不偷,我已经厌倦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进入距离李福信大院一里地的东山坳,周孜倦和薄三皮停下来整理装备,做行动前的最后准备。就在这时,远处的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,他们两个像小偷一样爬了下来,躲着偷窥。
不,有那么一瞬间,一个黑影朝这边跑来,三个人在拼命的追。那个黑影速度很快但不擅长搬运重物,把什么东西扔进了草棘深处,往南逃。追赶他的三个人正咬紧牙关往南跑。不一会儿,荒芜的墓地一片寂静。
在黑暗中,周孜倦将手指移向薄薄的三张皮囊,他们两个后退着去寻找影子扔进草丛里的物体。周孜倦眼疾手快,差点走直线去拿被遗弃的军用包,称重。
“感谢上帝,我不给福新添麻烦。”
“肉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?”
“不好说,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吧。”
。。。。。。
天亮之前,他们两个在杀猪三皮的窝棚里肆无忌惮地笑着,陶醉而得意。灯下鼓鼓囊囊的军用包就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。他们抽着烟,思考着,看着。投机的过程似乎是一种享受。他们非常高兴和兴奋。是谁偷走了李富新,让他们白享用了?
“重,不会是人头吧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,那就只能这样了。”脸皮薄的笑容满脸都是,笑起来不知足。周孜倦回答说:“我想是的。”
这是什么?
他们两个又笑了。
抽完一支烟,我开始用三层薄皮打开。里面没有真钱,但里面有白色颗粒,像药丸一样。周孜倦掏出一块舔了舔,闻了闻,道:“传言全是真的。李福信是个毒贩子。”
我踩到屎了,很臭。
“眼下什么好?”
皮薄有点害怕,知道这东西烫手。
周孜倦尴尬,瘦三皮搓着手不甘心。“你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
“我还能做什么?这东西不能动,这东西有无穷的烦恼。”
“好吧,好吧,我知道了。”
其实薄三皮也没什么好提倡的。周孜倦的眼神更是苍白,转身无奈的叹息。这就让周孜倦想起了那条身体前倾下水的鱼。是什么样的暗示?
周孜倦神沉思了一下,冷冷的走了。
薄皮叹气,左顾右盼都想不通,很像看着银子变成水的赌徒,一次次叹气,一次次露出不甘。
。。。。。。
半夜,周孜倦回到家,发现月华一夜未归。我很累,意识到岳华第一个想到的吴基池最近来衡阳了。
不是小家子气。总之,周孜倦感觉很不好。想了想,想出了一句问候的话,于是拿出手机拨通了金色KTV的值班电话。岳华接了电话。
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
周孜倦嬉皮笑脸的说:“我梦见你了。”
岳华很快回应:“我感受不到你的梦想,但我看到我脚下没有一寸土地,没有一片瓦片。”
意思是你没有感受到某人对爱情的深情,没有看到某人努力工作,却看到某人衣食无忧,整天无所事事。
事情就是这样。一个临时工守着一滩水有什么不好?
周孜倦发自内心的说:“对不起。”
“好像该轮到我说:对不起,我让你受苦了。”
月华像这样的半句话,总是让子累无言以对,总是让子累感到惭愧甚至惭愧。
周孜倦我觉得难过,但沉默中总是这样。我一直认为事物是对立的,感情也是对立的,但我想不通感情不能对立。
说到牵扯,周孜倦很想说:我让你牵扯进来了,我的爱人。
。。。。。。
黎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游泳,夜很深很黑。
李富新的院子里已经亮了灯,小雄和江小川或站或坐在李富新的眼前,尤其是小雄,他吃黑,吃黑货。他策划实施了这批货。现在事情出了问题,货没了。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小雄不知所措,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李福信喝着茶,思虑再三,做了一个应变调整。
“小雄,你现在可以带与会者去南方避一下,而江小川会留下来。就是这样。”
天亮的时候,李福信吃了两片安定就睡了。
。。。。。。
冬天。
潮湿的南方有着与北方不同的寒冷,北风卷起的寒流闯入衡阳。即使是来衡阳的北方人也会害怕这种又冷又瘦骨嶙峋又潮湿的风。
高原上的风是冰冻的,即使在阳光下,它依然肆无忌惮。
幸运的是,天气阴沉,没有风。
秃顶的小来到横山,而小受京都瞬昌实业的风云人物胡东明的委派,直接来到了李瑟娥阜新。
李福信只能硬着头皮顶上。
光头张三是他四年前的死党李福信;小张宗为是李富新崇拜的经典女性。
李富新是一个怎样的人?胡东明看得透彻。他一眼就看穿了不要脸的李福信在吃黑。胡东明权衡利弊,考虑暂时放他一马。有足够的时间让新账旧账慢慢跟他计较。现在他还是要承受。
胡东明的意思不言而喻。小张宗为撮合张三过孙,于是抬了个像样的梯子,请他李福信,威仪地逼他从墙上下来。
有一句很体面的话,大家可以聚一聚就走。
不然这就是先礼后兵的节奏,暗示你能吃黑我也能吃黑。
李福信头皮发麻,捧着茶杯,一脸苦恼,听和小说,他可从来不吭声不接话,得过且过,听人说,听人劝,听人申斥。
算是一种迂回吧。李福信见多识广,一耳听到另一耳,却不以为意。
“在衡阳这块土地上,胡东明认为没人有胆子碰你的生意。”张板着脸说,“我同意你的尊重。在衡阳,你,李福新,就是一座巍峨的大山。”
这时候的阿谀奉承,就相当于用一屎盆子扣李福信的头,让李福信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。
小张宗为下巴尖细,笑容亲切,说话也急促:“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说衡阳的李福信吃了北方的胡东明?”
对于这一点,李富新回答说:“这不可能是废话!”
“你在胡说八道吗?”
小张宗为回头温柔地看着李福信,说:“我们以后就走,走了就不回来了。衡阳变成一潭死水也没办法。”
张三,光头,站了起来。李福信放下茶杯说:“死水,说得好!至于臭水,我想李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唉!这恰好发生在尊重准备改变其路线的时候。过了这个村,就没有商店了。小雄可能会这么想。”
“小雄拿了货?”
三张嘴,萧瞄了张三一眼。很明显,李福信是在他的圈子里玩的,张三哥很健谈。
“别被小雄这个王八犊子给办了!张,你看这牛犊往那里去了?”
小把话说透了。“李福信,李老板,是你的人,你的人就是你的事。”
“对,没错。”
李福信说着,拿起茶杯,小张宗为失去了耐心:“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和胡东明谈。电话里说不清楚,可以北上京都慢慢聊。”
李福信放下茶杯,问了一会儿。
事情很复杂,大家都在动脑筋。
小张宗为淡淡地看了一眼,既不接受也不拒绝,模棱两可地和张三一起离开了李福信在东山的豪宅。
李福信端起杯子微微喝了一口,看着他们两个离开。这样衡量小张宗为的离开是不明智的。胡东明洗漱完毕。你有没有想过他李福信会去哪里?
——问神容易,送神难。
当然,胡东明没有义务对他李富新负责。
。。。。。。
刮风的太阳感觉不到有多冷。
小张宗为和张三走出李富新的东山坳,到了衡阳外的三环,故地重游。张三是衡阳人,小张宗为也是衡阳人。
小张宗为十三岁的时候,随父母去了京都,今天回到横山,这里的一切已经完全改变。
一路上,光头张三心不在焉地说着李福信,而看着路过的出租车的眼神显得不耐烦。
小张宗为会意地一笑,道:“三哥不用陪我了。”
“那我——”
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拍了拍自己光秃秃的脑袋,然后说道,“原来如此,所以单独行动,有事可做啊”
伊然轻轻一笑,没说话。
杨有个光头张三的情人,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