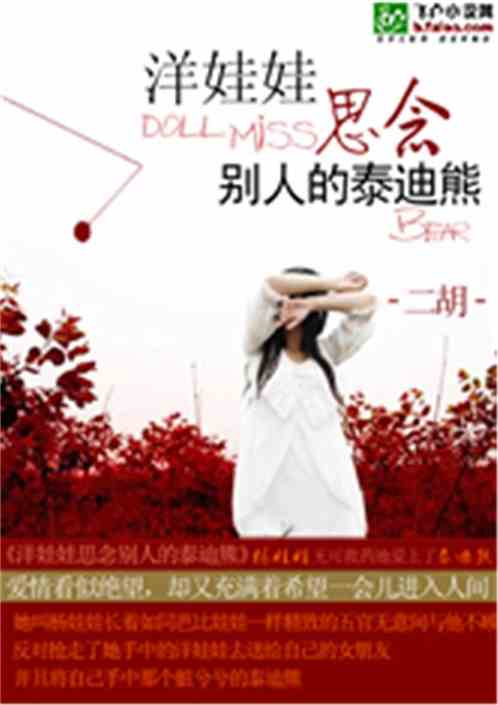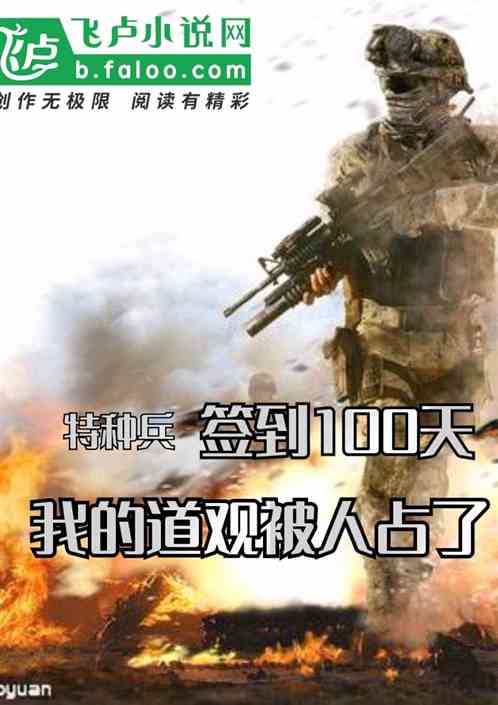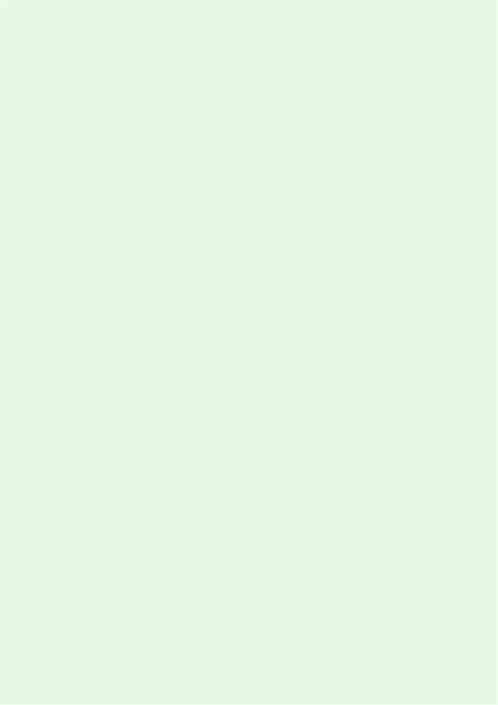“你看到了什么?”
信号好像不太好,耳机里的女声有点模糊。
“化学仪器,人工生命的遗迹,和...人体。”男孩低沉的回答很快就被外面越来越大的雨声淹没了。白色剑道服的下摆滴着水,随着他的步伐使劲摇晃。
“明白。援军被堵在五公里外,请小……”
砰的一声,有一个声音掉在了地上,它的余音在下一刻被切断了。
“怎么了?根!坂本!”
一声巨响,但在五公里外作战的士兵眼里,他们连一星半点火光都没抓到。
只有沙尘、泥土和石头掩埋了一切。
——————
铃声响起时,早阪樱正在为她的副手安排学院节的工作。
“哦,真对不起。”那种一如既往的完美微笑让副手感到不安。
她打开手机盖,一个熟悉的名字,还有一条彩信。
但是发彩信看起来不像那个傻哥哥会做的事。带着隐隐的疑惑和难以抑制的期待,她按下了“打开”键。
啪嗒一声,手机从颤抖的手中滑落,粉红色的六瓣花吊坠断成两半。
——————
雪白的长发在奔跑与停滞的缝隙中飘动,微卷尖端的银光流转。
左边是明亮的光,右边是深深的黑暗。在无边的混沌中,回荡着灰玫瑰永恒的歌声。
她在变幻的光影中睁开眼睛。
“迎,好久不见了……”微笑晕倒在那张近在咫尺的俊脸上,琥珀色的眼睛仿佛凝结了朝阳的温暖。
“一点也不。”然而,白毛女却完全不为所动,那双已经失去光泽的黑眼睛对准了那双迷人的眼睛:“在一个盲人面前有意义吗?”
“瞎子?”他冷笑道,柔和的线条瞬间从那张脸上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不羁的色彩,纯净而强烈,歇斯底里令人望而生畏。
他向后一靠,在虚无中双腿交叉稳稳坐下,晃来晃去的手掌里轻轻托着一只水晶高脚杯。微微摇曳的酒是暗红色的,黑暗的根倒映在血淋淋的涟漪中,随意扭曲伸展。
“在我的世界里,我有权允许盲人‘看’。”
“不管你此刻是否能‘看见’,盲人不再需要依靠‘看见’来认清真相,而且——”何颖举起手里拿着一个朴素的白瓷杯,在清澈的茶水上,鸟儿的翅膀扫过天空。
“这是我的世界,纷繁多样。”
繁秋眯起眼睛,盯着喝着绿茶的女孩,侵占她脸颊的灰黑色线条划过她嘴角,似曾相识的倔强线条。半晌,他忽地清声一笑,又站了起来。
“你看不见,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学?”他俯身在女孩面前,骄傲地咧着嘴笑,抬起手掌穿过女孩的手臂,遮住了被灰黑切成碎片的脸。
但是,手只是停留在光影被眼睛确认的地方。手心不会有触感和温度。就算沾了色,虚荣还是虚荣。
沉睡在记忆之海中的声音又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。
——“谁不能被感动,谁不能被感动?”
“时间到了,后悔还来得及,任性的羔羊。”
何影微微仰起头,那双双目却在一瞬间清澈如镜,隔着一段汹涌的时间,映在其中的轮廓又粗又扭曲,像炽烈的烟火,像狂野的泼墨。
她抬起同样布满黑线的手臂,食指和指尖掠过胸口,慢慢落在眉心。
“啊……”于是她黑曜石般的眼睛里勾起了戏谑的弧度,仿佛燃烧的虚空裂开了一道狰狞的伤疤。
高脚杯轻轻碰了一下白瓷杯。
天空中的白鸟向夜空展开翅膀,枯萎的树枝在夕阳下翩翩起舞。
两种颜色的涟漪上荡漾的声音清脆悠长。
——————
她在灿烂的朝阳下睁开了眼睛。
让五指稍微动了一下,苍白的右手僵硬地抬起,握住君麻吕伸出的手臂。她从床上坐起来,细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。
温暖的光线透过落地窗照进房间,提花窗帘在微风中轻轻飘动。
风暮和Ulchiola坐在靠窗的沙发上,她微微下垂的银蓝色的眼睛里隐隐闪动着文字的苦涩。
“准备已经完成,时间还有一个月左右。”君麻吕轻声回答了她没说的问题“对方应该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目的了,我们不用再担心了。”
“我明白了。”穆峰闭上眼睛,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低声报告说:“有消息从朱淮。两天前,在雷族长‘外出’期间,有六名重罪犯越狱,其中包括三名土人、一名火宗人和两名混血土人。具体身份尚未公布。”
何颖闭上眼睛,慢慢抬起下巴。她喉咙上一个狰狞的螺旋形疤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和消失。
叫她罪人的人都拿不走她的命,更别说她的声音了。
这一次,他们在黄昏时听到的是喉咙里发出的声音。胤祀天竺真实的声音沙哑而轻盈,就像夜空中的笛声,平凡而空灵。
刚才乌尔奇奥拉似乎心不在焉,这时她把绿色的眼睛转向声音的来源。
“总共,他们中的四个人将在半分钟内进入你的感知。以色列,他们也接近目的地了。”
她在君麻吕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。虽然她的脚步虚浮,但她不屈的脊背还是给人一种从容的力量感。
“就像君麻吕说的,不用担心。请做我的剑。”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