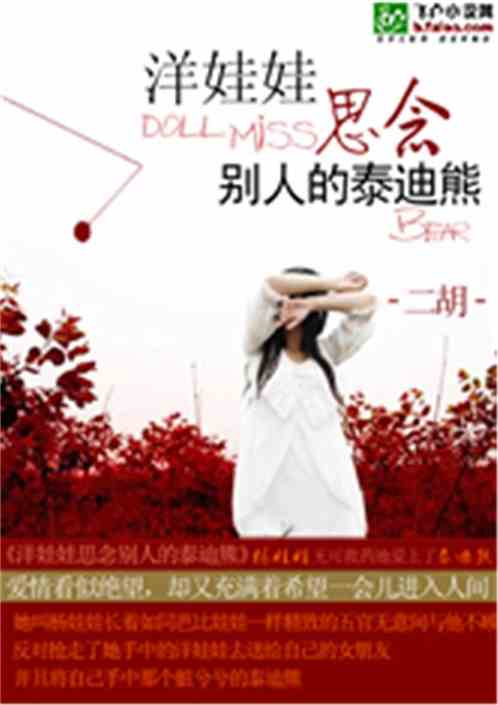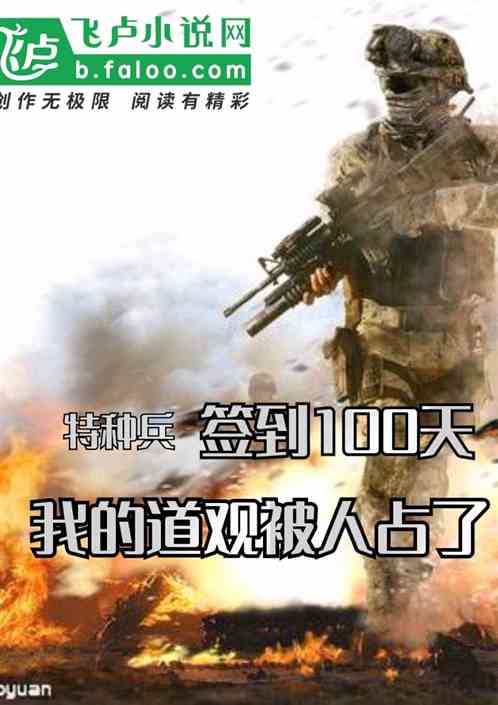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冬夜。
极地的寒风凝固了海水,切断了这座城市与世界沟通的动脉。暴风雪中,这座在荷兰尚属首次的繁华城市,终于呈现出罕见的寂静和萧条。大雪遮住了城市的灯光,挡住了屋里的噪音。城市里回荡的只有风的呼啸和破冰的声音。稀疏的人影在街上穿梭,把自己裹得像个球。
艾伯特是一个普通的荷兰人,也是这个雪夜为数不多的行人。他蜷缩在他的皮大衣里,诅咒着令人讨厌的天气,寻找一个可以取暖的酒吧。一想到火辣辣的朗姆酒穿过喉咙,他就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。
“咚咚,咚咚……”好像是踩在雪地上的声音,又好像夹杂着金属的碰撞声,神奇地压倒了风,在这个世界上清晰可闻,引得路人驻足观看。艾伯特我不禁忘记了酒吧和朗姆酒,好奇地看着声源。
一个身影在雪地里渐渐变得清晰——是一个男人,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。多么坚强的人,却是个傻瓜。看清来人,艾伯特不禁叹了口气。没有人会怀疑一米多高的人的爆发力,但是...这么大的雪,人光着膀子走路真的正常吗?只见那人只穿着一条薄薄的裤子,一件运动背心,上身戴着一顶帽子,看起来是两百年前的古风。在帽子的阴影下,我看不清他的脸,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艾伯特总觉得帽子下面有一堆锐利的眼睛在四处扫视。那人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竹盒,走路时似乎总是闪着金光。
他走得很慢,寒冷的空气似乎没有让他感到一点不舒服。雪花在他周围飞舞,但没有一片能碰到他的身体。
突然,他停了下来。艾伯特他觉得自己的目光似乎汇聚到了角落里的一个雪包上。他走上前去——似乎加快了脚步——他在雪包前蹲下身子,伸出手,扫去了飘起的雪花。
天啊艾伯特我差点没哭出来。原来是雪包下的老婆婆!我看到她所有的衣服都破损了,布满了晒伤和烧伤的痕迹。老人蜷缩起来,闭上了眼睛。只有从她颤抖的身体才能看出她的生命并没有消失。
那人伸出手,紧紧握住老人的双手,仿佛要把自己的体温传递给老人。艾伯特摇了摇头——老人已经被埋在雪地里很久了,意识早已丧失。即使他被发现了,他也无能为力。这个人的努力只是没有用——艾伯特叹了口气站到了一边,却没有发现自己站在雪地里这么久——围着这个人。
“孤儿院,孩子们...帮助孩子……”是错觉吗?艾伯特感觉自己一定是疯了,他居然看到那个垂死的老婆婆睁开眼睛,握着那个男人的手说着什么!
“带我去。”那人开口了,很难想象,这么坚强的人,竟然会有这么柔和的声音,在这冰天雪地里响起,让冬日的风有了一丝春风的味道。
先不说艾伯特在那里胡思乱想,那人已经摘下帽子,露出了脸——出乎意料的年轻,出乎意料的稚嫩,绝对不到18岁——这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想象的坚强的人,还是个少年!
那个人——不,现在应该叫少年——轻轻地把帽子拿到老人的头上,扶她起来,向雪地深处走去,渐渐消失在艾伯特的视线里。艾伯特我正准备追上去问点什么,一股冷风吹来,他剧烈的颤抖了一下。“哦,该死的!”他迅速走开,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和其他路人一起一头扎进了路边的酒吧。
“奇怪,怎么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?”酒吧里的酒保擦了擦杯子,从他刚刚望出去的窗口走开了。“奇怪,我是怎么到窗口的?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一夜之后,风停雪落,初升的太阳把没有温度的光洒在刚刚苏醒的阿姆斯特丹。雪反射着阳光,将整个城市笼罩在金色的光辉中。市民们出去清扫积雪,有说有笑。黎明的阿姆斯特丹是圣洁的,宁静的,祥和的。
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,醒了艾伯特。他从酒吧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揉了揉因宿醉而疼痛的头,一步一步走进了光线里。报童开心地跑过酒吧门口,撞上艾伯特。
报童抱歉地笑了笑,继续往前跳。“好孩子,走路小心点!”艾伯特喊了一声,他笑了笑,才做出生气的表情。他微笑着摇摇头,转身离去,迎接新的一天的生活。
谁也没有注意到,一张报纸从报童的包里掉了出来,一阵风把它吹了几下,脸敞开着躺在地上,只看到第一版的上面写着——
“头条:本市孤儿院昨晚被烧毁,全院无人居住!”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