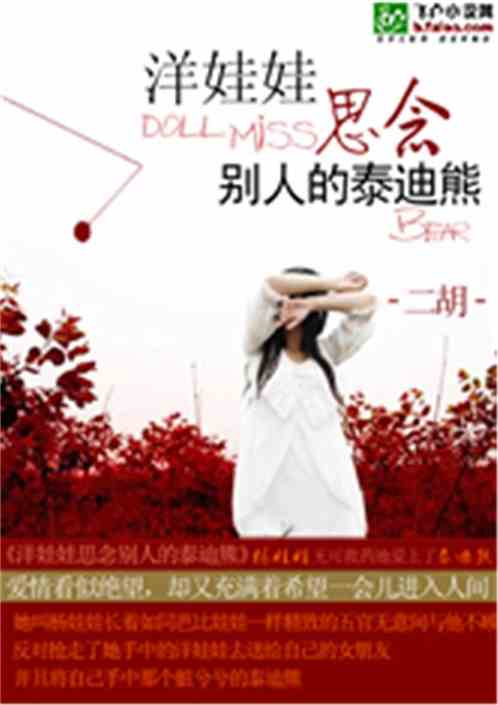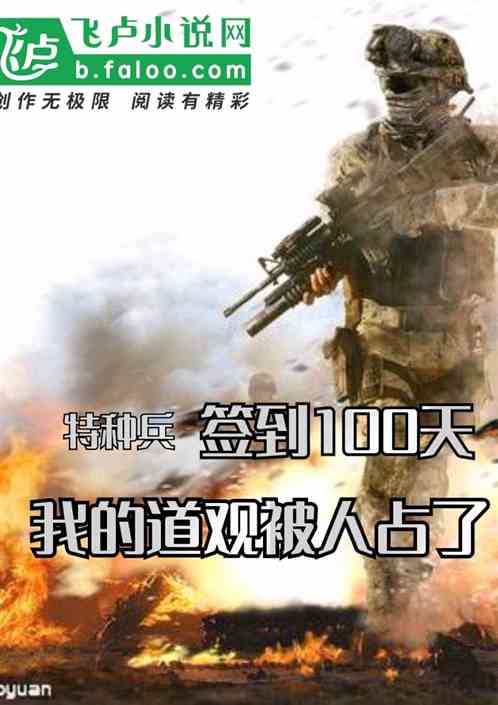这是一个扭曲的世界,它不属于我。
从天上往下看,终年积雪的净土山一片白茫茫,一群人正慢慢走向山顶。
姑娘们从高处静静地看着,看着他们像散落在雪地上的黑点一样向前移动。
她把三棱军刺放进鞘里,对着手掌叹了口气,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,戴上口罩,向山顶跑去。
《净土山之谜》
我把窗帘拉到一边,看着洞外肆虐的大雪。雪花拍打着我,提醒我这不是梦。雪中的岩石突然站了起来,伸出粗壮有力的手脚刷去积雪。它让我回过头来。它的小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,由裂缝构成的嘴巴紧紧地抿着。我害怕极了,赶紧放下窗帘,拉过毯子盖在身上,坐在那里瑟瑟发抖了一会儿。
前几天我用望远镜看到远处有两块“石头”在打架。积雪和碎石四处乱飞,轰鸣声随风而来。山顶的雪层崩塌,瞬间吞噬了他们。我幸免于难,因为观察位置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山顶的山洞。
没想到在现代21世纪生活了这么多年,又变回了山顶洞人。
我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,“石头”已经不见了。就在刚才,它在空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,除了风雪,没有别的声音。这座山上的雪下得很大。从醒来到现在已经三天了,一直没有停过。前段时间,我趁着风雪的短暂间隙,四处看看。除了我,周围没有人。几个小时后,暴风雪又来了,所以我不得不原路返回。
我手里拿着茶坐在火堆边发呆,很想找个人问我这是什么地方,是谁带我来的,为什么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都变了样,是在地球上某个未被发现的地方还是世界末日后的地球?还是仅仅改变世界?
洞内井井有条,衣食住行一应俱全,洞壁明显是人工加工的。虽然是在山顶,但是出奇的温暖,只是有点简陋,没有接触工具。
唯一的电力设备是电灯和多功能加热器,可以用来做饭和烧水,但没有发电机。还好,取暖器的电池很给力。当我醒来时,它的电量只有三分之一,直到现在还有一丝电量。
看来这个世界的科技应用要比我熟悉的世界超前一点。不,不,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。现在被大雪困在山里,进退两难。我现在还不确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,我都快疯了。
我挠了挠头,沮丧地看着镜子。玻璃里映出的人形不是我,而是一个黑发黑眼的少年。我摸了摸镜子里的眼睛,大吃一惊。
我从没见过谁的眼睛那么纯黑,好像所有的光都被吸进去了,没有一丝折射。十八九岁的脸算不上英俊,但也英俊耐看,只是眉眼冷冷尖尖的,没有表情的时候,就像这山上常年不融化的雪。我敲镜子,“他”敲镜子,我嘲笑“他”和我穿一样的衣服,除了这是现在的我,我不做他想做的事。
远处有一个圆圆的仓鼠形状的生物背对着我坐在桌子上。它大约有一只金毛小狗那么大。它会发出噼啪声,时不时会发出一点静电。它胖乎乎的样子总让我想起皮卡丘...当我醒来的时候,它站在我的头旁边,脸上带着非常人类的表情。她见我坐起来了,就跳到我怀里开心地蹭来蹭去,还给我端来两杯还热着的茶放在桌上解渴。
这几天,它是唯一和我同住一室,同吃同睡的生物。多亏了它,我才不会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发疯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愿意把我那一点点粮食储备的一半给它。
我检查过我的身体。我左臂两处受伤,右臂一处受伤。我心上的致命伤就像被三角军的刺扎了一下,至今还结痂。疼的人直喘气,但是这几天疼的太快了,已经看不到了。我试着回忆,但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没有和我分享这个身体的记忆,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复活的。
“你知道皮卡丘吗?”我看着仓鼠。皮卡丘是我给他起的名字。无论如何,他们看起来很像,没有第二个人会听到我这样叫它。
仓鼠茫然地看着我。
"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而不精确的推理."我找出一支笔和纸,把我知道的写在上面。
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本日记,就是我现在用的那本。里面的文字和原世界的文字只有部分相同,我读起来很吃力。这三天勉强看了几页,大多是一些事情的简短记录,但可以看出写日记的人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对外界和他人的描述很少。
根据叙述,这个房间...这个洞穴的主人显然就是这具尸体的主人,不久前在这里被杀害。没过多久我就复活了,因为醒来的时候茶还冒着热气。
“啊,真麻烦!”我一下子趴到桌子上,郁闷了一会儿,勉强打起精神去想。
没有太多挣扎的痕迹,要么是熟人动手,要么是被秒死,但作为一个生活在雪山中的孤独者,应该对外人的到来有所警觉,但有两杯茶,说明他招待了对方。不确定是不是朋友,但至少认识,说明这个人身边有一个或几个人不可信。同时,社会性和礼仪性也没有被抛弃,日记中也有与他人互动的行为。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人类群居生活。
.....当然,如果他有给自己倒两杯茶的怪癖,我也承认。
凶器不是意外而是军队刺伤。如果有凶器,有控制的人,但是附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,说明有外国人来过。
综上,我主观认为是外面的朋友出于某种原因把他送给了KO。
“真麻烦...长时间呆在这里不合适。谁知道凶手会不会回来查。”我把日记扔进背包,关上门,塞在厚重的窗帘里,滚到床上,拍拍大仓鼠的头。行李早就打包好了,天一晴我们就走。除了不安全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粮食储备快用完了。“又要入夜了。晚安,皮卡丘。”
睡觉前,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。漆黑的山洞里,只开着电暖器,温暖的日光灯映衬着洞外的风,让人感觉温暖了一倍,食物和电都快要断气了。
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。我像一只鸵鸟。当我遇到危险时,我可以躲起来。如果我不能隐藏,我会把头埋在沙子里。如果我不努力,我将永远不会前进...只是这次藏耳朵没用。
这是一个扭曲的世界,它不属于我。
我蜷缩着,累得闭上眼睛,在一大堆烦恼中睡着了。
第二天醒来,周围很安静。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,终于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。
一直呼啸的风消失了。我突然跳下床,推开门,掀起窗帘。阳光像一把利剑射进来,划破黑暗,仿佛那场永不停息的雪终于结束了。
我眼花缭乱,抬起胳膊捂住,另一只手摸索着墙壁,试图回到洞里。
有人抓住了我的手,手指纤细而冰冷,是一只女孩的手。里面有茧,但是手背很光滑。她粗暴地把我拖进洞里,捅了我一刀,撕了一些布,蒙住我的眼睛,在我的后脑勺绑了一个扣子。“在黑暗中呆了这么久竟然还敢马上出来,眼睛不想要了吗?!"她骂着,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,声音冰冷扭曲,像是戴着面具在哼唱,还故意打开了变声。
我冷冷,这是谁?原主人的熟人?四周都是雪。为什么我没听到她来了?该死,有熟人上门我该怎么办?这个女孩似乎脾气不好...我脑子转得很快,最后决定再鬼混一段时间。被发现的时候,我选择了最烂大街的借口,假装失忆。
“现在就去,五十年的雪期快结束了,联盟的人要来看你了。”她又把我拖出去了。“没时间等你的眼睛恢复了。这些人已经等了这些年了,他们甚至在雪期完全结束之前就闯入了这里。”
“疼疼!!"我胳膊上的伤口被她撕得好像要裂开一样,我疼得大叫起来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她说话冷冷的,明显是在吼,但声音里没有火星的味道。反而冷得像冷风吹来的刀子,好像她看不起任何人。“就是几个刀伤,忍忍吧。”
“我的心脏上也有刀伤。我要是分了,我就完了……”我不敢反驳她,只能小声说。虽然我完全不知所措,但我还是知道我有麻烦了,只有这个脾气暴躁的女人,比如月经,可以依靠我。
她的动作似乎停顿了一下,她转过身来,摸了摸我的胸口。
“轻轻碰一下。”我心有余悸,怕她会使劲按。
“实际上有伤口...不是梦。”她喃喃自语,不相信地甩了甩头。“这是谁干的?联盟的人已经来过了?”她抬头看着我。虽然看不到,但我就是注意到了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“什么是联盟?”我不能再假装了。“不知道是谁干的!”"

 已完结
已完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