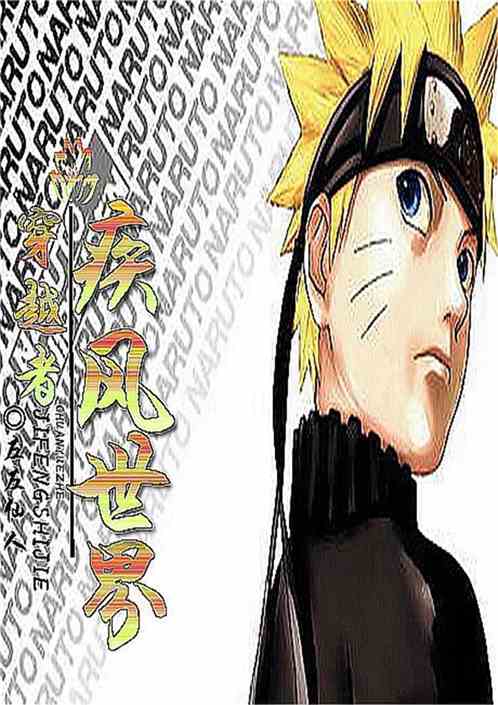《的哥》之八 免费试读
雨势越来越紧,坑坑洼洼的路面逐渐积水,而且随着不断的往下流,排水不畅,有的地方,雨水甚至演变成了一滩。汽车飞驰而过,溅起水花。如果这是本田这样的进口车,无疑是马力强劲、动力十足的象征,对车本身没有任何威胁。就算有,也是那些小怪,一般都有一百九,因为积水确实阻碍了他们的行驶速度,让他们觉得有点压抑。然而,如果死水是针对国内汽车,尤其是像鲍晓这样的出租车,这将是可怕的。俗话说,一物降一物。因为它的高压线圈无保护,低,又恰好离左前轮很近,雨水很容易溅出,但如果胜利线圈沾上导电的雨水,脾气暴躁的发动机很快就会罢工,导致其他机构把车放在一边。无论多么恳切司机恳求爷爷告诉奶奶,它都会充耳不闻;即使你再愤怒,再暴怒,它也会巍然屹立,在革命中坚持到底。总之,想都别想离开。到时候可以看司机站在齐腰高的水里,咬紧牙关,用尽全力推车。简直惨了。反正司机不然这种面包出租车是不会轻易离开它的位置的。所以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,大街小巷总会看到遇难者颓废的身影。如果你看埋伏车里的司机,他更沮丧,眼神暗淡,情绪低落,很无助。
被称为工作狂的夜灯,今天也不例外。据说他的面包出租车并不是因为溅水才停下来的,但是这个雨天是全方位的考验,尤其是轮毂刹车的小面,面对雨水有一个更可怕甚至是致命的弱点,那就是刹车片碰到水不会立刻刹车。为了安全起见,他把车停在了路的拐角处。他隐居在车里。这时,我用手指夹着万宝路,望着窗外瓢泼大雨。在狭小的空间里,尽量舒展放松自己,因为这也是一个休息的机会,而他淡然的抽着烟。
突然,右前门被外人拉开,一个人未经车主同意直接坐进了车里。这时,外面的“夜雨”比以前慢了许多。只听那人一声令下:“岗洼城。”从他的语气判断,他说话很冲动。因为他那个地方人多,七八公里,一般人司机不喜欢去。看来司机要是敢拒载,马上就有回应了。要么举报,要么动手,总之不好。
司机听了他的约会,伸手去拿插在点火开关里的车钥匙,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右侧车门是否被乘客关上。一不小心看到别人,他眼睛一亮,惊喜地说:“你!哦,车在哪里?”
“在你后面。”
夜灯把头伸出窗外,转头向后看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车后面停着一辆微型面包出租车,但是牌子不一样。而且他车上的乘客不是陌生人,是比自己更早加入京兆出租公司的马春丽。
挑水人问车主:“车怎么了?”
“没什么。”夜灯回答道。
“那你为什么潜伏在这里?”
"躲雨休息一下。"
马春礼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龙泉牌香烟和打火机,看了一眼正在抽烟的店主,抽出一支叼在嘴上,点燃香烟,深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沮丧地吐了出来,再甩出一句:“刚才真倒霉。”
夜光明漫不经心幽默地问,“山西煤还是陕西煤?”
“再赞助200名警察!”说话间,我从兜里掏出了足够的证据,十张20元的当场处罚票,所有的证人和物证都在。夜很亮,我就接过来看了看。然后我又恢复了刚才的表情,说:“别忘了,你是我们公司的头号违规学者。你给警察惹了什么麻烦?”
“嘿,你说多了孙子,刚才从平安拉一个去龙潭湖,到东直门大桥的时候,我就感觉声音不对,心说佛祖,你别出去了。在桥下往上爬的时候,“噗——”呛了一下。恐怕我什么都有了。我七上八下的,我对自己说,别坐以待毙,打起来,差点把马达弄坏了,也没用。请爷爷告诉奶奶,这不是一个大日子。我想下来看看分电器和高压线。我刚打开座椅和后盖,我在偷看。我听到身后有人说:“修得好吗?" .我高兴的像个傻逼,以为是熟人或者我们公司帮了我。回头一看,旁边停着一辆清障车,坐在上面的正是那顶大帽子。钩子一挂就被拉出人行道,多说也就20米。路边停车,死孩子扔了,和收据一起撕,200韩元!一整天的收入!都贡献了。我一想,连砖都没那么贵!嘿,你说的很好。我找遍了所有的小路,但什么都没发生。当我再次点火的时候,车着火了,这他妈的没把我逼疯。唉,今天出门好像不太合适。我出去的时候没看历书...汽车着火的时候我们走吧。哎,我刚走没多远,然后就看到了清障车,拖着一辆旧吉普。我经过雅婷的时候,副驾驶座的警察跟我一起按喇叭,点头,意思是谢谢你筹钱。我浑身发抖。我真想砸了这辆破车。气得肚子疼。唉!我也看到了,赚了这点小钱,早晚得放在医药费上,到处漏风,门都关不好。现在这辆破车开得我满地找牙……”
可能是那位害怕发表长篇大论的先生背过身去。还没等观众激动起来,情绪激动的同事讲完了,夜灯打断了对方的陈述:“共和国不会忘记灾区人民需要你。”
“唉!做牛马难,做苦行僧难!!!"
“年轻人”夜灯模仿着老年人的语气说:“受一点苦就不要抱怨,不要那么悲观。别忘了,太阳在云后,很快就会苦尽甘来,永垂不朽。”
“刚才说回家,又不是来看你的。我以为你也上瘾了。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马春礼抖抖崭新的票子,放回皱巴巴的口袋,又道:“把这一天的收获报告给你老婆。”
寂静的夜光相互瞥了一眼。
“今天是23号,我还没有得到足够的!不过,我们经理不错,死不了。如果我哥的黑龙能换下来,公司一天都耽误不了,就那个贼操的经理,更别说不是人操的了。出门在外,交货当天收工。不想出去,就打车回家拿钱。”
寂静的夜晚明亮的眼睛盯着窗外。从外面的景象不难看出,世间万物都是对称平衡的。哭了就笑,伤心了就开心。此时,那些拥有1.6分李霞或更高等级、更高价位的车型正在经历久旱逢甘霖,如鱼得水。因为这个节骨眼打车的人特别多,下雨天赶着回家,所以到处都是。主要是很多车都出局了,所以这个时候高价车爆满,所以车的能量很足。他们从南到北毫不顾忌雨水溅到分电器上,因为设计合理周密,根本溅不到;它们是盘式刹车片。走积水路面,刹车灵敏度一点都不打折扣。因此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,手指间夹着著名的万宝路,有时还会带着味道吸一口气,轻松地听着甜美的周华健,与乘客交谈时发自内心的微笑似乎让人感到更加迷人和光荣。时不时轻蔑地瞥一眼路边同事唱歌被强制下线的包子。我的眼神是那么的清爽和骄傲,表情仿佛在向同事们说教:你傻吗?这次看着我...
“差多少?”夜灯问他的哥哥。
“怎么弄五百。”
“500够吗?”
“差不多。”
“我明天再去拿500。”
“两天了,没事。”
“嘿,完了,省的想着这匹马。明天我先给你戴上。”
“那就好。你今天怎么样?”马春丽问夜灯。
“两百。”
“可以,够顺滑的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出来的?”
“八点钟。”
“我可以在六点钟,大哥。”
“现在太难做了。早上我,哎,从亦庄到正义路走了一趟,开始放空。什么和平门、宣武门、西便门、白云寺最后到东直门才拉?太他妈邪恶了。将近一个小时没人去了。他妈的皇冠被拔了。我,一个天津包子,不理狗,把它放在横坡上。只有有人挥挥手,去了大山子,苦啊。苦不如不吃。后来9点多拉回了京广。早上阴天,闷热,气压低,赶上了这条机场辅路。过了半个小时的灯,在这辆车上,我乐得卖起了蒸饼,整整一个蒸笼。”
“看看李霞。”黑夜的明亮眼睛引导着春风和车窗外的自满。
“唉!用大网抓大鱼。今天是他们的国庆节。”突然,马春丽似乎想起了什么,对着一旁的夜灯自言自语道:“昨天我正在努力,发票不见了。去公司换了两本书,在公司呆了一会,和老盛聊了一会。他也刚从管二局开会回来。我们互相交谈,有一种新的精神要传达。下个月,我们将开始增加份额,60的小面和李霞一起。”情况越糟,绳子越紧..."
“被宰了!”
“也是个棋子,比这厉害多了。是不是又有一个关于我们公司那个倒霉鬼杨黎明的故事?”
“前两个月最后一次被几个男生碰伤的那个?”
“对,就是他。”
“怎么又冒险了?”
“这一次,我不仅被打了,还得给人赔钱。”
“你把自己打了,还给人家钱?”夜灯奇怪地问道。
“是时候和盛局长谈谈了。我说点点(北京话:去)。刚走,他和家人去了公司。这下惨了,那张脸印象深刻,看起来就像面团馒头。左眼闭着,右眼勉强眯着,青一块紫一块,嘴歪着;他一瘸一拐的。他看起来更老。这是怎么回事?我听到了几个词。他,呃,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东部高地拖到其他地方。那是200块钱,不远,六七十公里。这样不好吗?那个婊子实际上是在钓鱼。他太笨了,不会知道的,街上的女人说。快点,家里有急事。他长得相当漂亮,所以被厄运赶走了。之后那贱人说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,你可以跟我去拿。他一想进去就进去了,他就跟着进去了。进屋后,小妖精叫他在外屋等着,他进里屋拿钱。等一会儿,小子,可以开开眼了,那个婊子,上下混杂,乱七八糟,妆就这样和坏人争着撕,头发长长的,脖子上还有掐痕……”
“就像你看到的那样。”
“他说,我这是鹦鹉学舌。说着说着,就听见母狗喊:抓坏人,抓强盗——就这两个声音,小子。三四个从外面进来。我想我一直在外面憋着。进来就打不起来,拳打脚踢,踢得不够远。最后被扶上车,送到派出所。那婊子去车站,恶人先告状,哭得死去活来。你说什么?更何况你说人家不信。内外勾结,一伙人,刑讯逼供,不招也得招。最后黑警决定让他回家拿钱——五千,等他回去再拿车……”
“出租车都搞定了……”突然,夜灯腰间的BP机尖叫起来。他把它从腰带上的名片盒里拿出来,举在面前。他伸手摸了摸红色的按钮,查了查信息,然后大声念道:“明天白天多云转晴,最高气温33度。”报告结束后,另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:“六点了。”
“再给他们一天时间。”懒散的马春礼打开车门,下了他的黄包车。无精打采地站在地上,然后疲倦地伸了两个懒腰,放松了僵硬无力的四肢,然后无精打采地自言自语道:“整天真无聊。”疲惫的眼睛环顾四周,然后坚定地说:“走——回家。”转身垂下虚弱的头颅,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自己的车上。